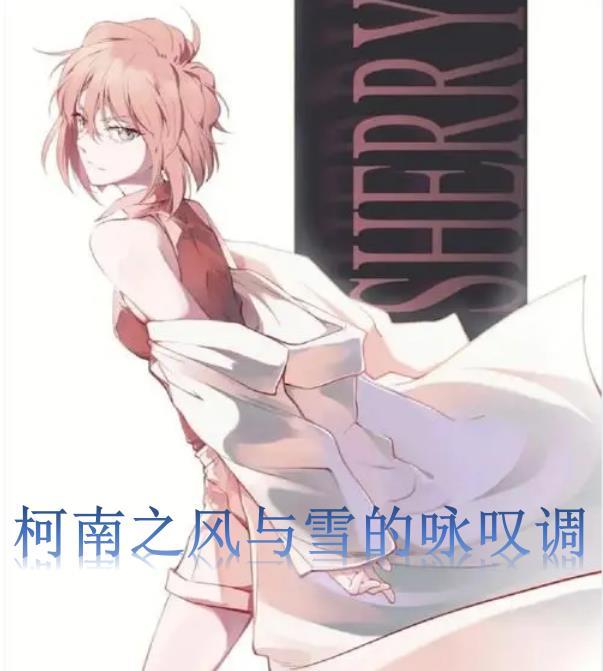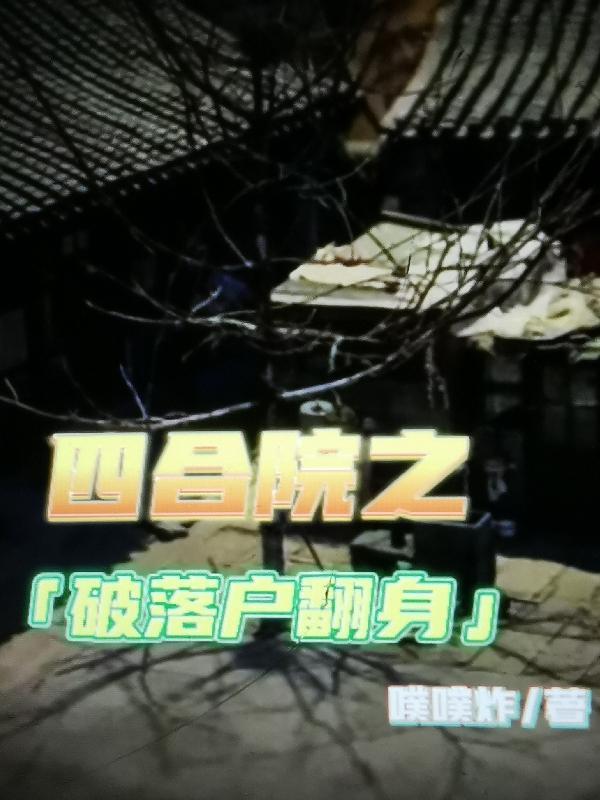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小满生活演员表大全名单 > 第98章(第1页)
第98章(第1页)
小满朝堆成山的供品里扫了一眼,痴男怨女,拜神仙,求姻缘,供的东西也千奇百怪。
她伸手从里头抽出一本册子丢在文貍眼前:“你愿不愿意帮我个忙?”
“什么忙?”
“为我做一回红娘。”
天又下起绵绵阴雨,初春将近,这几日雨水渐多起来,过了午后,茶铺客人只三两个,宋攸闲闲坐在柜台打着哈欠,宋柳忆见状便朝他手臂拍了两下,没想到自己背后也同时被人轻轻拍了拍。
她回头,身后站着个妇人,体态丰腴,约摸四十来岁,满脸堆笑。
她认得此人,这妇人乃是城东一带的媒婆,走街串巷包打听,好几年前也曾给她说过媒,因她身有残疾就打算昧着良心将她介绍给一个满脑袋癞头疮的京城地主做小妾。
宋柳忆自然不会给她好脸色,正打算请她出去,媒婆倒先开口了:“姑娘可别急着赶我,我是来吃茶的,喏。”
她从袖子里掏出铜钿先付了茶钱,宋柳忆沉下气也不好说什么。
等把茶汤茶点送过去,媒婆笑吟吟一把牵住她问道:“周小郎君可在里头呀?”
宋柳忆皱了皱眉,露出疑问的神色,媒婆笑道:“这小郎君可了不得,我早就听闻他在弘英书院那一众子弟里出类拔萃,今年科考大有希望啊。”
宋柳忆微微点头,冲她浅笑了下,媒婆喝口茶立马切入正题:“你看,他前途无量未来一片大好,这不就有瞧上他的人家了嘛。”
宋柳忆一讶,拿出纸笔就飞速写起来。
【他妻子新丧,怎可提这种事。】
“新丧不也一个多月了,年纪轻轻总不能孤家寡人一辈子。听好了,那家人是城里的富户,女儿生得花容月貌还是个大姑娘家,娶进门非但不亏还有了丈人家的帮衬,若是以后进了官场什么的总要银子上打点打点吧。”
宋柳忆摆手,还要下笔,媒婆心急嫌她写写画画耽误功夫,于是走到里头拉了个伙计过来翻译,碰巧捉的是出来收拾碗碟的阿七。
宋柳忆要拦却苦于说不出话,媒婆又像个连珠炮语速奇快,一来二去,阿七很快听明白了意思,当即愤然道:“我家少夫人才走,少爷怎么可能立马再娶!”
“哎哟,又不是什么坏事,那等我见了他本人再说。”
“没什么好说的!”
阿七气呼呼地请她出去,婆子不依,又说起那户人家买卖做得如何之大,姑娘又如何贤良淑德、秀外慧中。结果阿七通通一口回绝,婆子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嚷嚷道:“你这小厮真不识好歹,我是为他以后做打算呢。”
阿七一句不听,强拉着媒婆往门外赶,婆子扒拉着门框不肯走,两厢拉扯中,铺子外有人跨过门槛走了进来,恰是从书院回来的周词。
媒婆反应极快,上去就攀住他说道:“巧了不是,周小郎君回来了。”
周词诧异地看向她:“你认得我?你是……”
“这一块有谁是我刘媒婆不认识的,小郎君,我正有事找你呢!”
她开门见山,舌灿莲花,宋柳忆同时在她背后对着周词打手语【她为做媒得钱财,别听。】
周词看在眼里,但到底好涵养,耐着性子等她说完,只摇头说了句:“太荒谬了。”
“别回绝得这么快嘛。”
媒婆拉着他继续絮叨,“先夫人去了,你还好好的,日子总得过下去吧。我大字不识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什么沧海……沧海难为水,除了巫山它都不是云,听听,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啊!可我也听说了,后来写这句的人没过多久又续弦娶妻,一路平步青云了。说到底,郎君以后是要做事业的,身边还得有个温柔贤惠的贴心人不是?”
周词平静道:“多谢好意,但此事绝无可能。”
见他软硬不吃,刘媒婆也没了耐心,嘴里阴阳怪气地嘀咕道:“还真把自己当个情种了,送上门的机缘不要。”
周词蹙了蹙眉,如此反倒不再客气,他直着背脊垂眼看向媒婆:“要考虑也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媒婆眼神一亮,立即换了副笑面孔:“郎君你说。”
他嘴角扬起一抹哂笑,字字清晰地说道:“亡妻在我心中分量极重,她死后我此生不复娶妻,只纳妾室。她生前最恨旁人对她不敬,妾入门后,初一十五需向她排位焚香祝祷,逢年过节要往她坟前磕头拜祭,若那位姑娘能做到,我便不再推辞。”
“这……”
刘媒婆面露难色。那富户是几年前从下九流到一夜暴富,压根没读过书,女儿更是大字不识,但穷惯的人发了横财容易小人得志,更想找个有才学的入赘拔高门户,又如何肯伏低做小当个妾,还要给死人叩头跪拜?
周词静看她脸色红一阵白一阵,脑门上仿佛写着唯利是图四个大字,他心底嫌恶,轻蔑一笑:“告诉他们,这个条件若答应不了就不必多说了,请吧。”
周词伸手将半边大门敞开,阿七跟上将另一边也打开了,宋柳忆见机朝婆子背后一推终于把她彻底撵了出去。
经此一遭,周词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回来后一直坐在窗前对书发愣。
连续不断的雨滴轻敲在屋瓦叶片上,淅淅沥沥,声声入耳,久了不免勾起一阵倦意。
周词默默叹了口气,放下书,随意地趴在桌上小憩片刻。
阿七端着泡好的新茶给他送去,隔窗见他枕书而眠,转身又把茶水放回去,蹑手蹑脚进屋拿了件厚衣来。
阿七刚小心翼翼地将衣裳披至他肩头,周词突然伸手攥紧衣料,他睁开眼,呼吸急促,直起身看向窗外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