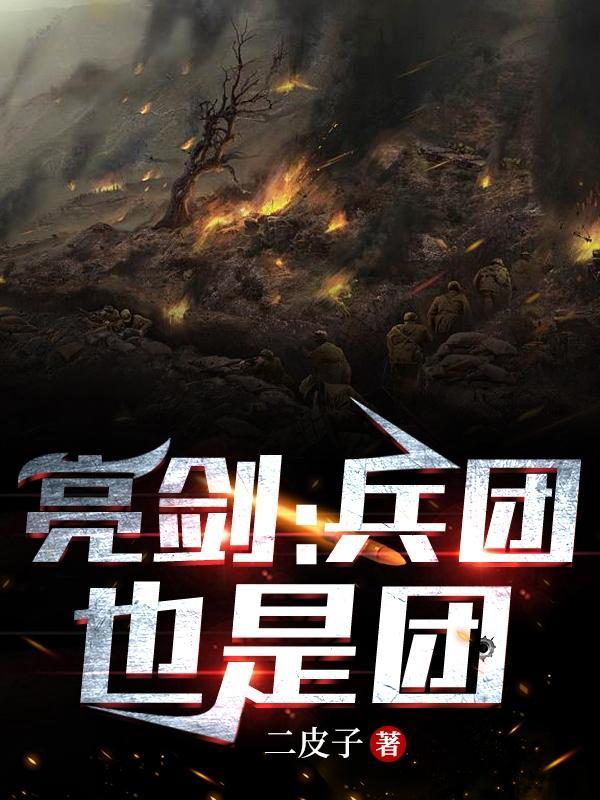69书吧>枯木逢春言情阅读 > 第98章(第1页)
第98章(第1页)
“侯爷,侯爷你糊涂了。”
谢祈昀:“东西是你们准备的,人是你们家的,你们便是诚心要害我的名声。”
害他的名声,让他在老裴相面前失信,再偷走证据册死无对证,真是好计谋。
“吵什么?大清早的你们是要闹成什么样?当我死了吗?”
时机正好,老裴相一脸愠怒,拖着沉重的步子而来,身旁还跟着多日不见的梁怀夕。
谢祈昀一个箭步上前,赶在二人进门之前把人挡在了门外,没叫他看见里面的情况。
先一步开口,“老裴相,我已查明事情真相,证据在此。”
说着,他将证据册呈上。
另一本虽不知所踪,但眼下证据全不全已经不重要了,他需得尽快把孙鹏处理了。
既然是你们先不仁,那便休要怪我不义。
沈霜提心吊胆地跟出来,却只见老裴相翻看证据册脸色越来越阴沉。
半晌,他吩咐下人,“叫孙知府来。”
随后又朝着梁怀夕拘了一礼,“还请王爷做个见证。”
谁料到梁怀夕根本没在听他讲话,眼神全注意在屋子里沈南迦地身上。
“老师,侯夫人受了些伤,不如先让我为侯夫人包扎一下伤口吧。”
久病成医,他自然是通晓医术的。
老裴相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谢祈昀赶忙一步都不敢落地跟上,其后又陆陆续续跟了一众吃瓜中的裴家人。
屏风之后,梁怀夕凝视着伤口,眉心紧紧纠结在一起。
他一只手撑着沈南迦那只受伤的手,另一只手灵活从袖中拿出伤药,一点一点洒在上面止血,谨慎程度堪比某种精雕细琢的大型工艺。
沈南迦有自己的计划,她不说,他便不问。
他以为自己能事事料到,能处处为她安排周全,可这个人就是最大的变数,她向来狠心,不顾及自己。
昨夜在那清居堂中,待他赶到之时,见到的却是沈南迦把自己整个人都浸在满是冰块的浴桶之中。
她不知道服用了什么,即使是被冰块刺激到打哆嗦,浑身的皮肤也泛着异常的红。可即便是痛到极致,贝齿将嘴唇咬的血肉模糊,也没喊出一声来。
他抱着她冷了一夜,才堪堪将那药性降下去。如今一早,只几炷香不见,她又受了伤,见了血。
你怎么又将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梁怀夕在心中暗暗的疼,只恨自己不能替她受这些。
止了血,上了药,他用干净的帕子包扎好伤口,抬眼对上沈南迦灰蒙蒙的眼睛。
她哑声,道了声谢。
昨夜神志不清,但模糊间有个人始终没离开过,她知道是谁。
梁怀夕眉眼间的愁和心疼化解不开半分,鬼使神差抬手触了触那极艳口脂之下伤痕累累的唇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