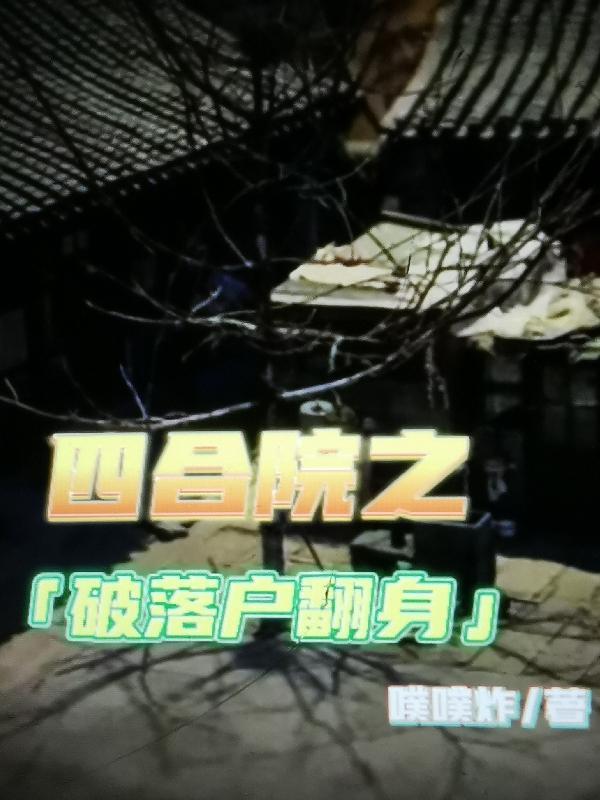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养父女演员表 > 08罚跪(第2页)
08罚跪(第2页)
时间慢慢过去,一开始,覃珂还有心思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可渐渐的,她膝盖就撑不住了身子,那疼一开始是涨,后来又变成了麻,最后成了难忍的剧痛,带着肌肉时不时的痉挛。
最可怕的,是她对时间毫无概念。
她没办法知道自己究竟跪了多久,还要跪多久。
在这种未知中,她知道的,以及能体会的,只有无尽的疼痛和害怕。
本来止住的情绪又有了崩溃的迹象,覃珂受不了的弯下了腰,背也挺不直了,身体歪歪斜斜,要不是后面有墙体在撑着,怕是下一秒就要倒了。
覃霆在余光中看到了她模样,他扫了眼时间,四十分钟没到,就受不了了?
她不肯出声,在那强忍着。
只是原本被他修的板板正正的身体歪了,肩也保持不住水平,左边比右边低了一头。
房内热,她跪在那能照到光,本来湿着的头被晒得半干,尾微微卷曲,在她的腰腹处轻轻扫着,很痒。
被光一晃,她人白得亮。胸前的肉色也变得很浅,太嫩了。
她还是个小孩。
十七岁。
未成年。
她是,他的女儿。
覃霆的喉咙干,他往下咽了咽。
他现,自己在不自觉间,已经切换了角色。
只听“咚”
得一声,覃珂再跪不住,人朝前摔在了地上。
这下是真摔结实了,她前胸着地,两团的奶肉被压得扁平,多余的溢出来,擦着地的那沿儿登时就红了。
她趴着看他。
双唇微微张开,似要说什么,可什么都没有说。
他不允许她说话。
覃霆的视线重新挪到了覃珂身上。
父女两在无声中对视着,一高一低,一上一下。
不平等的姿势,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关系。
覃霆看到了她被数据线蹭红了的手腕,他绑的根本算不得紧,是多嫩的皮,只是拴着就出了痕迹。
他站起身,给她扯开了绳结。
“自己起来。”
覃霆说。 覃珂垂下眼,她松了松腕子,两手撑着地,一声不吭的爬起来了。
还没等站稳,她双腿又是一酸,眼看着又要摔下去。
覃霆伸出了手,抓住了她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