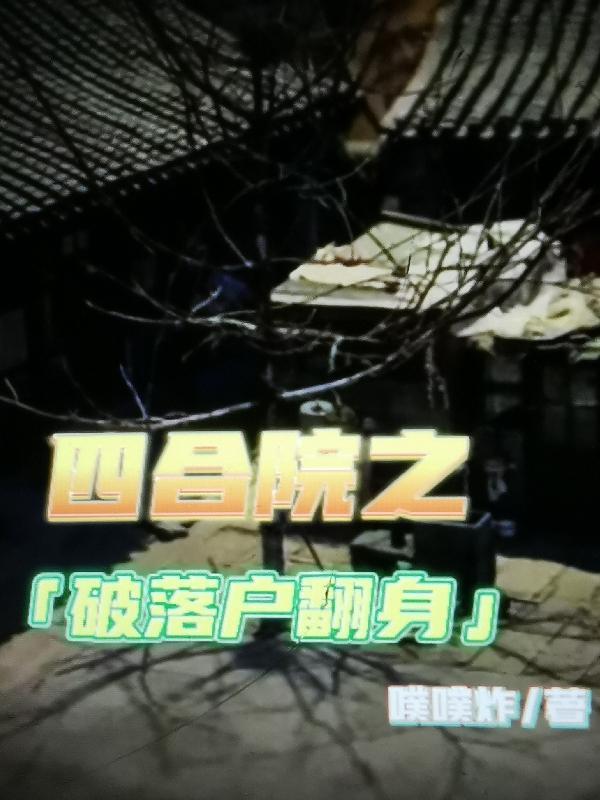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墨实不黔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在巫医的医庐之时,魏瓒其实是醒过来一阵的,那个脸上有图腾的人告诉他,这个叫小果的孩子答应了充当药人试药,才换得了医治他的机会。
魏瓒当时问他是试的什么药,那人笑得阴恻侧的,说你放心,这小孩儿命硬得很,上回他试药之时吐了半碗血都活了下来。
魏瓒怒不可遏地说不用给他治了,那人说了句那可由不得你,随即他就被一块沾了麻药的药帛给按住了口鼻。
“你这个小崽子,是不是傻的?”
,魏瓒看着眼前失去活力的小人儿,喃喃地骂道,“你怎么敢的?那么大一头狼扑过来,你不怕吗?自个儿才这么大一丁点儿,就敢去替我挡。”
魏瓒出身显贵,又长在皇宫,打小接触的人不是对他恭恭敬敬的,就是带着各种面具,连儿时要好的玩伴都因为各种原因渐渐疏远。他幼年失恃,而他的父帅常年在外征战,一年到头都难见一面,从未遇到过一个不因他的家世背景就对他好的人,就连那些在战场上拼死守护他的侍卫都是受了他父帅的嘱托。从来就没有人仅仅是因为他魏瓒这个人,而豁出生命去护着他,只有这个叫岑罪果的异族孩童,萍水相逢却不惜舍命相救。
他不应该是任何人的罪过,也不是因罪孽而结出来的果实,他应该是被捧在掌心中最珍爱的硕果。魏瓒心里这么想着,手便取下了出生后就戴在脖颈上的那条银链,银链上有个机关小锁,他拨开了关窍,小锁应声而开露出了里面藏着的一颗药丸子,他将丸子塞进了岑罪果的口中,用食指往小孩儿喉咙眼儿里一戳,药丸就顺势被吞了进去。
魏瓒没忍住又捏了捏他绵软的脸颊,说道:“世上唯一的九还丹,我们魏家的保命药都给了你,你一定要活下来啊,不然剪了你的小麻雀。”
魏瓒看着岑罪果又长又浓的睫毛无意识地簌簌抖了几下,就趴在床边看,像得了个大玩具一般,一会儿摸摸人脑袋一会儿捏捏人小手,没一会儿自己也玩累了,攥着岑罪果的手就在床边睡着了。可能在这一晚,命运的红绳就牢牢的系在了俩人的手腕上。
三日后岑罪果醒了过来,只觉得喉咙口都要冒烟了,因不知身处何处,小动物般的警觉令他没有马上出声,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明白过来自己可能是被人救了,帐子里没人,但实在是太渴了,他忍着后背火炙针刺一般的疼痛挣扎着爬了起来,发现自己浑身光溜溜的,周围也没见自己的衣裳,便将毯子披在了身上,小心翼翼地撩开帐帘一条缝往外张望,就看见帐外不远处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人焦急地说道:“少将军,你怎可以将这保命的药随意就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蛮族小童呢?”
然后就听见另一个声音回到:“他并非来历不明,是他救了我的性命。”
岑罪果认得这是小阿哥的声音,那个陌生焦急的声音继续说:“瀛州被围,魏家军在几次突围战中死伤惨烈,连军报都很难传出来,眼下最重要的是少将军要尽快带兵驰援瀛州城。”
魏瓒点头交代了几句,眉宇间一片肃穆,脚下没停地随那人匆匆走远了。
岑罪果缩了缩脑袋,心想着他们说的那个保命的神药,是给我吃了吗?
片刻后军号响起,外面的各种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人声夹杂着马蹄和兵器的碰撞声纷杂成一片。岑最果不敢贸贸然走出帐子,身上又疼得厉害,只能躺回了床上,舔了舔干裂的唇,蜷缩成一小团,一个人默默地熬着。
好在过一会儿进来一个小药童,见他醒来显得十分惊喜,跳起来说是要去叫军医,岑罪果虚弱地“嗳”
了一声,那人已经跑没影了,他嘟囔道:“能不能给我口水喝啊。”
没过一会儿那小药童又吧嗒吧嗒地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说道:“我都给搞忘了,军医他去了前线。你居然这么快就醒了,他说你没个十天八天的是不可能醒得来呢!竟然三天就醒了,真是太厉害了。”
,这人倒豆子一般,自顾自的说个没完。
岑罪果哑着嗓子:“这位小师傅,有劳给口水喝成不?”
那药童才想起来炉子上还煨着药,连忙将人扶了起来:“我这就去给你取水,等会得喝药。”
连干了三杯水后,岑罪果总算是缓了过来,连声道着谢。药童手一挥说了句:“没事,听说是你救了我们的少将军,那我自然是得好好照顾你的。”
岑罪果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嘀咕道:“你们的少将军就是小阿哥吗?”
还没等药童回答,帐帘就被掀起,熟悉的声音传来:“他们的少将军便是我。”
岑罪果一抬眼就看见魏瓒换上了一套锃亮崭新的银甲,威风凛凛地大步走了进来。
“小阿哥可真俊吶!”
,岑罪果将心中的赞叹脱口而出,有点害羞地捂住了嘴,缩着肩膀傻乐。
魏瓒见小孩儿醒了,还恢复了些活力,便过来捏了捏心心念念的软包子脸颊,道:“我这就要出发去助我父帅一臂之力,临行前过来看看你,见你醒了我便也放心了,这里是我魏家军的军营,你且安心住下,药童会留下照顾你的。”
,魏瓒指了指旁边的小药童,那药童忙应了声。
岑罪果乖乖地点了点头,说了句好,又想起魏瓒腿上被毒物咬伤的毒,便问道:“小阿哥,你腿上的蛇毒可解了?你们族中的巫医可找得到狼吻草?我族巫医说此毒一定要用狼吻草才能解的。”
,他想起巫医给他的种子,着急忙慌地想要掏出来,结果掀开毯子,才发现自己光着屁股吶,顿时闹了个大红脸,赶紧拉着毯子往身上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