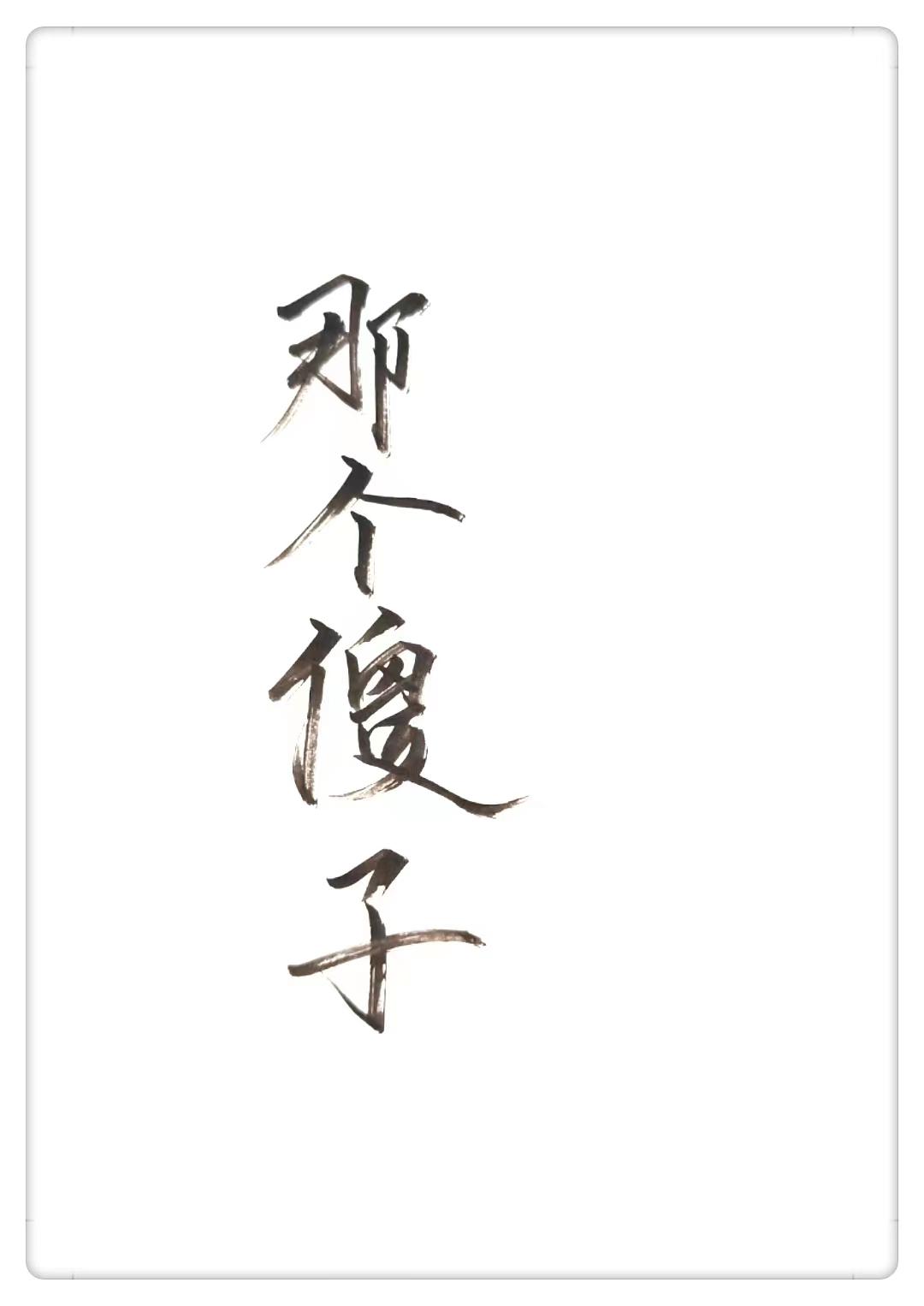69书吧>民国三十年灵异档案免费阅读 > 第27页(第1页)
第27页(第1页)
戴笠就这样默默地和张鹤生对视着,处变不惊。“怎么死的?你说!”
张鹤生喘着粗气。“死在了皇姑屯,日本人下的手。”
“不可能,你又骗我!”
张鹤生怒气冲冲。“我说了,我没必要骗你。张作霖遇刺身亡,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儿。不信,你出去随便拉个人问问。看看是我在骗你,还是你自己骗自己。”
戴笠说道。“人,我肯定是要问的。你先说,现在是多少年?”
张鹤生问道。“一九三七年。”
戴笠回答说。“不,不,现在不是一九二七年吗?”
张鹤生面露惊诧。“你进jīng神病院的时候,是一九二七年。这都十年过去了,你觉得,还是一九二七年吗?”
戴笠冷笑。张鹤生呆滞的松开了戴笠的衣服,将他放了下来。看看屋子,再看看自己的衣服,脸上的表qíng瞬息万变。“我做了十年的疯子?”
他空dong的眼神,求助般的瞥向每一个人。第三十二章十年(2)“是的,直到刚才,你都还是个疯子,只是现在,突然清醒过来了。”
杨开说道。他完全可以理解此刻张鹤生那复杂的心qíng,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张鹤生声嘶力竭的举起手,指着戴笠的鼻子:“我明明还在张大帅的列车里,保护他返回东北。”
“哦,我明白了。”
他自言自语:“我现在一定是在做梦,你们都是梦寐,在蛊惑我,对不对?只要我醒来,你们就都没有了,我就在列车里了,我就又看见张大帅了。”
“这个世界上有种可怜人,他们把梦境当做现实,把现实当做梦境。说好听点,是庄周梦蝶。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纯粹的懦夫。”
说到这,戴笠突然上前一步,狠狠地bī视着张鹤生:“都十年了,你还想继续逃避下去吗?”
“再逃避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人生又有几个十年,二十年!”
“我……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真的什么都记不清了”
张鹤生带着哭腔,逃避着戴笠的目光:“我不相信,你们合伙骗我这个老实人。我要到外面去,我要一个个问,他们才会对我说实话,就是这样。”
说完,他跌跌撞撞的朝着大门走去。“义父,我拦住他!”
曾养甫说道。“不用。”
面对着张鹤生清瘦的背影,戴笠淡淡的说道:“这十年来,你都在jīng神病院里,活在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枷锁里。但你知道外面生了什么吗?”
“这十年来,小日本的僧侣,yīn阳师分兵两路,一路专门破坏各地的地运,另一路专门破坏各地的气运。地运破,百年荒,气运破,千年凉!时至今日,已有近三个省市的地运遭了殃。”
当戴笠这句话说完之后,张鹤生踏出的前脚竟硬生生的收了回来,随即蓦然的转过脑袋。“当真?”
张鹤生满脸凶戾之色。“当真”
戴笠点头:“还有些事qíng,你想听吗?”
“说!”
他咬牙切齿的说道。“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活捉了其中一名参与者,竟现对方其实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
张鹤生眼珠子一翻:“如此汉jian,誓杀之!”
“听我继续说,这个人不但是个中国人,还是你们‘中华抗日救亡祈福协会’的原成员,隶属于全真教。我们起初也不信,严刑拷打之下,这才水落石出。原来,东北失守后,整个全真教就投了敌,小鬼子yīn阳师之所以能如此轻车熟路的到处搞破坏,全是因为他们带的路。”
戴笠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可能,我们都是过誓的,为国家尽心尽力。”
张鹤生一口否定。“誓,这个年代,誓言能值几个钱,能换来真金白银吗?”
戴笠冷笑。“还有,两个月前,我们现了你的那位老友,梁维扬的踪迹。”
“梁大哥,他不是死了吗?”
张鹤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哼哼!”
戴笠意味深长的瞥了他一眼:“不是记不清当时生的事了吗?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如此肯定梁维扬死了。”
“噫,我怎么会记得他死了?”
张鹤生自己都有些不可思议。“我想想,别说话,让我安静一会儿。”
张鹤生晃了晃脑袋,努力挖掘着记忆深处的谜团。“那天,是yīn天,天空有阳光,但很少。”
张鹤生喃喃自语:“那天,梁掌教和我说,离东北越来越近,小鬼子可能要下手了。叫我带着一批jīng锐弟兄协助大帅的卫队打头阵,队里有个主心骨,遇到突事件,也好处理。而他则亲自坐镇后方,保护大帅……”
破碎的记忆慢慢拼接,在张鹤生的脑海中形成一幕幕残缺不全的胶片。“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张作霖放下了手中的围棋:“谁?”
“大帅,是我,梁维扬。”
“开门吧!”
张作霖对身边的士兵招呼了一声,片刻,风尘仆仆的梁维扬走进了房间,他穿着一身泛白的长衫,下巴一撮山羊须。脚步稳健,太阳xué高高鼓起,显然是个高手。“梁大哥,你怎么来了?”
正陪着张作霖下棋的张鹤生惊讶的问道。“鹤生,前面可能要出事儿。”
梁维扬愁容满面的说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