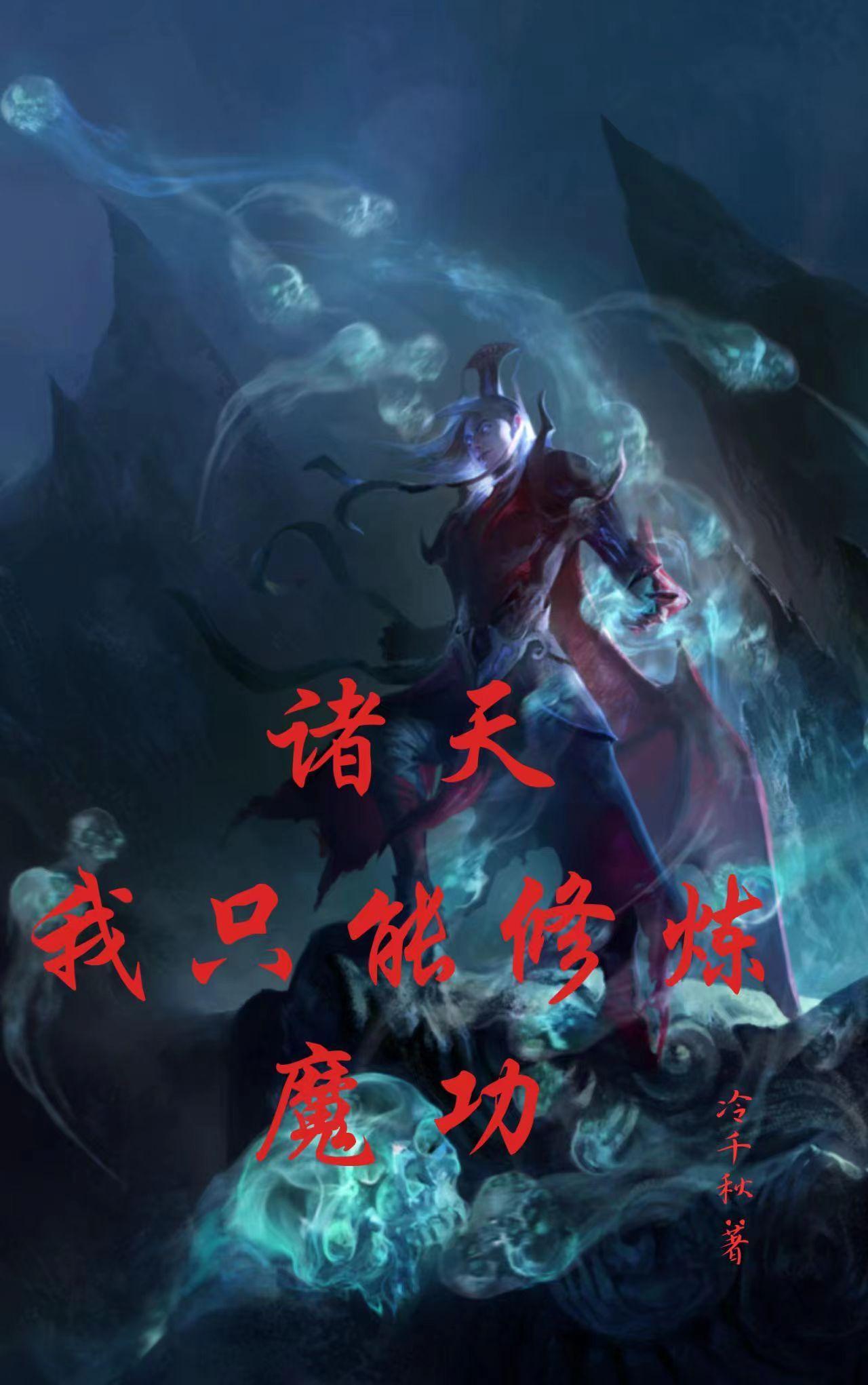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七爷番外续写 > 第54页(第1页)
第54页(第1页)
不知道是不是平安的错觉,只觉得自家主子这&ldo;外客&rdo;两个字咬得特别清晰,还老老实实地说道:&ldo;巫童说他会治,比太医院的御医医术高。&rdo;景七&ldo;啪&rdo;一下把书丢在一边,好看的眉头皱成一团,没好气地道:&ldo;那就说我死了。&rdo;一边小鸡啄米似的小丫头立刻醒了,睁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平安委委屈屈地跟个小媳妇似的打量了一下景七的神色,这才应声出去。景七自己干坐了一会,对一边的丫头说道:&ldo;去我书房里,把那本灰色账簿和西北布防图拿来,然后你下去自己玩去吧。&rdo;小丫头岁数不大,应了一声,不一会拿了东西进来,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期待地看着景七,等他点了头,这才欢天喜地地跑出去了。景七皱着眉打开了西北布防图,勉强压下心绪看了一会,随后在一边的小几上取了纸笔,写了封信,才吹干了,正封口,忽然床底下突然一阵悉悉索索的动静,不一会,小紫貂灰头土脸地钻出来,蹬着他的鞋蹦上了床,踩了一串小灰脚印。景七一把捏起他的脖子,将它轻轻丢下去。小紫貂在地上晕头转向地晃悠了一会,百折不挠地又要腻上来,被景七瞪了一眼,无辜地竖着小爪子蹲在地上抬头瞅着他,不动了。景七把被子上的灰拍干净:&ldo;我这忙正经事呢,看见你就烦‐‐自己玩去,别闹我。&rdo;小紫貂委委屈屈地晃晃自己的大尾巴,遛到墙角缩成一团,很是伤心。这会平安又推门进来,一眼看见景七脸色不善,抿抿嘴,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不往里走,说道:&ldo;主子,他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rdo;景七哼了一声:&ldo;孝子贤孙哪他?跟他说,爷死了用不着他收尸。&rdo;平安往外看了一眼:&ldo;您说这好好的,跟巫童闹什么别扭呢,从早晨都闹到这会了,这都晌午了,多大的事不能好好说说?&rdo;&ldo;不该你问的事少问,&rdo;景七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将手上的信封吹干了交给平安,&ldo;找个稳妥人把这封信捎给陆深陆大人,亲自送到他手上。&rdo;平安应了一声接过来,往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ldo;主子,您这么晒着巫童,就不怕他一会硬闯?&rdo;&ldo;爷那么多侍卫养着都是干吃饭的是不是,南宁王府说闯就闯,你当这是菜园子?说不见就不见,他爱等等去。&rdo;一抬眼看见平安还傻呵呵地戳在门口,景七更暴躁了:&ldo;你也快滚,别在我跟前碍眼。&rdo;平安咧咧嘴,悄么声地顺着墙根溜出去了。景七随手捡起一本书,打开以后看了半天,一个字都没看下去,一甩手将书摔在地上,正好滚到紫貂旁边,小貂警觉得往后蹦了一下,又凑上去闻了闻,景七长长地出了口气,闭上眼靠在床头上坐着。小貂大概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从窗口蹦出去了。整个卧房里就剩下景七这么一个会喘气的,安静极了。昨儿晚上他知道乌溪是喝多了,也知道这事麻烦得很,他摸不准今天一早,乌溪酒醒了能记住多少,也没想好怎么对付这人,便非常懦夫地打算躲一躲。乌溪自来起得早,自己也就在房里躲到他起来,自行回府就罢了。那么尴尬的事,乌溪若是酒醒了还记得,明智一点,就该悄么声的自己回去。可惜这位南疆巫童一点也不明智,这回还就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说都说出来了,也不藏着掖着,一大早就等在外面,要见他。景七起来一听说这阵仗,登时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想也不想地便让平安找了个托词回绝了,这不愿意见对方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乌溪也向来算是个识趣的,总该回去了吧?谁知王爷再一次低估了南疆巫童死倔死倔的驴脾气。此人大有债主风范,笔杆条直地一站,清楚明白地表示,你不出来,我就不走,一定得给个说法。眼看着日头已经爬上了当空,吉祥轻轻推门进来:&ldo;主子,传膳么?&rdo;景七扫了他一眼,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ldo;算了,才起来没多大一会,早晨吃的那点东西还在心里堵着呢,你们自己吃吧,我不用了。&rdo;吉祥知道他刚冲着平安发过脾气,这会儿也不敢触他的霉头,格外乖巧地应了一声,便要退出去,又被景七叫住:&ldo;出去跟巫童说,不留他了,让他先回去吧,等过几日我有精神了再跟他说话,再说皇上现在正在禁我的足,也不方便老见客人。&rdo;吉祥出去了没有片刻,院子里便是一阵骚动,景七皱皱眉,忍不住从床上下来,走过去侧身站在窗边,从他的角度,正好可以看见乌溪一个人在小院门口站着,像是吉祥和他说了什么,乌溪突然激动起来,要往里硬闯。侍卫得了命令,拦着他不让进去,吉祥帮不上忙,也在一边劝着。乌溪大声叫道:&ldo;北渊!景北渊!你给我出来说话!你既然都知道了,这会儿躲躲闪闪算什么男人?!你出来!&rdo;守着院子的侍卫自然不是乌溪的对手,好在乌溪也没打算伤他们,卸下他们的武器扔在一边,人敲了穴道让他们暂时无法自由行动。吉祥想拦又不敢,只得追上前去:&ldo;巫童,巫童!&rdo;没人挡路了,乌溪反而有些犹豫,在院子里站了一会,脸上的线条和拳头都绷得紧紧的,一袭黑衣裹在身上,像是一柄枪一样,站得笔直,说不出的倔强,定定地往景七这边望着。就他这个不依不饶的劲头,实在让景七头疼。他对付得了别人,是因为别人都有弱点,所有才能有乱花迷人眼。他生命中有无数的奸诈者、阴佞者、深沉者、有君子有小人,却从没有过一个乌溪这样直接、毫不犹豫、死不回头的孩子。景七伸手揉揉眉心,叹了口气,走出来,靠在门框上,淡淡地看着乌溪。乌溪被他的目光一触,有那么一瞬间,瑟缩了一下,随后便又挺直了腰板。&ldo;从早晨闹到现在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过几天说,吵得我头疼。&rdo;景七已经习惯了一张嘴,就开始东拉西扯地打太极。乌溪愣了一下,一点都不能体谅景七想给双方都找个台阶下的苦心,上来就道:&ldo;我昨天喝醉了酒,但是和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我也就是那么想的。&rdo;景七沉默了一会,到现在仍不大能适应他这种过于不含蓄的直抒胸臆,半晌,抬起头,表情很平静,却没再看乌溪,对吉祥说道:&ldo;叫人都下去,你也是,今天的话……有一个字传出去,别怪本王翻脸不讲情面。&rdo;抬出了这个语气,吉祥就知道此事不是闹着玩的了,利落地清了场,自己也退了出去。景七这才组织了一下措辞,转向乌溪道:&ldo;昨天晚上说过的话,我可以当没听见过,你回去吧。&rdo;乌溪急了:&ldo;说过的话就是说过,你也听见了,怎么能当成没听见过?&rdo;景七轻声道:&ldo;那是我的事,巫童,交情一场,别为难我……也别为难你自己。&rdo;乌溪僵立了半晌,才勉强说道:&ldo;你……是一点都不喜欢我么?&rdo;他对自己的情绪从来不加掩饰,那一刻眼神神色悲伤得仿佛瞎子都能看出来。景七突然就想起前一天夜里,那少年依着门,瘫软在地上,一声一声叫着自己名字的样子,心里一软,各种柔软委婉的托词在脑子里转了一大圈,却到底没说出口。他想这么长时间了,对乌溪是个什么样的人,心里也是明白几分的。这孩子天生就没长委婉那根弦,直接、锋利,那不如便直接以对,免得给他这样不切实际的希望,反而害得他执迷不悟,于是点头道:&ldo;你不要胡思乱想了。&rdo;言罢便要转身进屋,乌溪咬咬牙,在他身后大声道:&ldo;你总有一天会愿意和我走的!&rdo;景七猛地回过头来,一字一顿地道:&ldo;南疆巫童,你是公然撺掇本王里通外族么?&rdo;乌溪浑身一震,脸上少有的血色顷刻退了干净,景七一甩袖子,头也不回地道:&ldo;恕不远送了。&rdo;乌溪望着紧闭的房门,半晌,才自言自语似的对着空荡荡的院子说道:&ldo;你总有一天会愿意和我走的。&rdo;没了回应,不知景七是听见还是没听见。那天以后,景七就再没有见过乌溪,乌溪仍是每日下午的时候,来他府上坐上一会,景七不见客,他也不再往里闯,只如同景七去了两广的时候一样,每日在那里等待一阵子,便回去,风雨无阻。而南宁王的禁足生涯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被放出来了‐‐因为东平泰山地震了。金支葆乱碧霞幢,玉检泥崩青帝玺。五岳之尊,苍然万古与国并存之封禅重地,崩了。朝野哗然。而各派阴谋家们,也开始借着这个机会磨刀了。风雪世道赫连琪感觉最近很不顺心,自从南宁王景北渊那个祸害从两广回来以后,他就一直不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