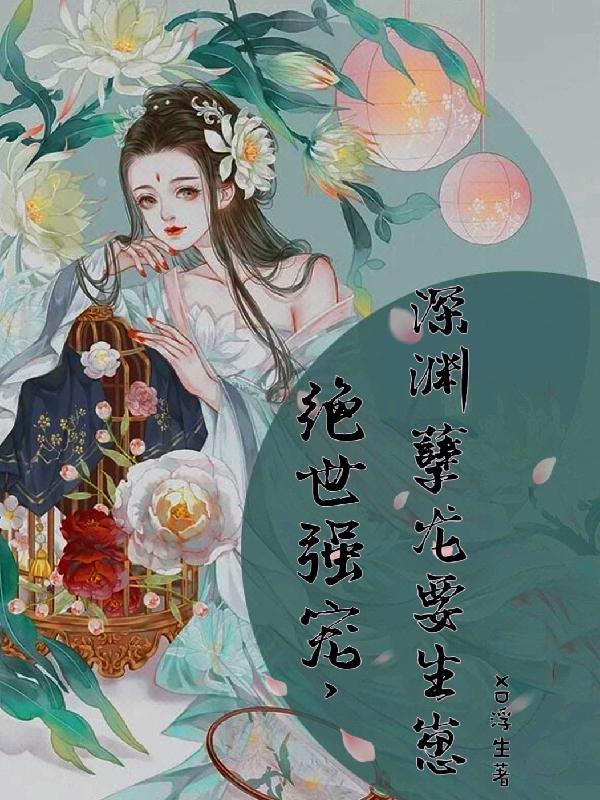69书吧>娇女养成手册免费阅读 > 第87页(第1页)
第87页(第1页)
姜慈绕着这方假山石看了良久,说道:“难怪上回我见到这里有那么多的碎石,怕是这孙大人在这动了土的,呵,亏他还美其名曰从什么江南运来的,其实,不过是些虚幌子,掩人耳目罢了。”
姜慈愤愤然,她看向韩玢,见他默不作声,便小声问道:“那个……韩大人……天色已亮,您赶紧走吧!”
韩玢笑了笑,上前抬手摸了摸她的头顶。姜慈不自然地微微往下一缩,欲说还休,不知如何回应韩玢对她忽转的态度。
他柔着声音说:“你先走,我看着你。”
姜慈听了,傻傻地一笑,赶紧点了点头,面色微微有些潮红,掉头便往自己的住处而去。此时她脚步轻快,身形摇曳,韩彬看在眼里,眼底止不住一些笑意。
哪知姜慈刚刚走上长廊,绕过拐角,便听见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韩大人?您怎么在这儿啊?”
姜慈一听这声音,立刻在长廊拐角处躲了起来,悄悄地探出一只眼睛盯着如意假山那处。
只见苏妈妈的女儿苏菱,款款而来,因偶遇韩玢,脸上止不住的激动与期待。而她姣好的面容,一丝淡妆,在简单素婉的衣裙下也掩不住少女的风采。
“苏菱姑娘怎么起得如此早?”
韩玢问道。
苏菱福了福身,低下头娇羞地说道:“我今日的早班,一会儿还要喂老夫人豢养的家兔呢。想着还早,便来这如意山石祈个福。”
韩玢摆出一副十分好奇的样子,似有笑意地问道:“此话怎讲呢?”
苏菱害羞地别过头去,小声细语的说道:“传说在乞巧节过后的一个月,来这如意石下祈福,便可得到白不相离的良人。”
姜慈看在眼里,酸味席卷,睁大了眼睛看着韩玢不拒绝也不接受,不知他为何不干脆推开苏菱。
只听韩玢问道:“我对你们孙府仿江南的园子也很是感兴。我之所以一早在这,也是因为觉得那传言似乎可行,便来这等一等我的那位有缘人。”
他有意无意地瞥向了姜慈藏身的拐角之处,只期盼姜慈能长点心听懂自己的意思。
此话一出,苏菱顿时害羞了。本就好看的面容带上了一丝绯红的红晕。只见她倏然上前,紧紧握住了韩玢的手,韩玢心底惊讶,想着抽手收回,哪知苏菱越攥越紧,竟死死不松手。
姜慈眼里,韩玢对苏菱的投怀送抱毫不拒绝,便越看越懊恼,看来这种官宦人家的公子还真的是惹不起,前脚撩拨自己,后脚就勾搭孙府的小丫鬟,真是得陇望蜀,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若不是此时此刻被苏菱堵着躲在这里,她还真的不知道原来韩玢是这种人。
大脑几乎不受控制地思考着,姜慈歪歪斜斜靠在长廊的白墙上,再也看不下去、听不下去韩玢与那个苏菱两个卿卿我我。
姜慈恼羞成怒地转身就走,只留下韩玢和满脸娇羞不已的苏菱。
苏菱似乎觉得韩玢没有拒绝她便是对她有不小的兴,与其在这孙府坐井观天一辈子脱不了奴籍,不如早知攀上高枝,哪怕混一个最末等的妾也是可以的。
想到此处,苏菱心花怒放,势在必得地将头靠上来,低低道:“韩大人既然对我有意思,那便跟老夫人讨了我去,苏菱必定日后好好伺候大人……”
说着,她的手竟然攀上了韩玢的脖颈,韩玢漠然冷笑了一下,低头之时,却已换上一副柔情蜜意的笑脸,他说道:“那便请苏姑娘帮我一个忙可好?”
苏菱几乎大脑空白,哪想的了那么多,此时此刻,她春心荡漾,只娇羞地点点头……
姜慈气鼓鼓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顾不得许多,一头钻进了被窝,将自己整个儿埋了起来。
这一夜生的事情,都那么的不真实,认甚至让她无法相信,韩玢的温柔和那个额吻不是自己的心魔。
本想找到了孙府的藏宝之处,拿到账簿能扳倒那个曹辅,哪知道那么巧,这孙耀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还将账簿带走了。
姜慈想着想着,困意席卷而来,便抱着被子沉沉睡去。
待再醒来之时,都已是日上三竿,她一把掀开捂得烫的被褥,有条不紊地穿戴梳洗穿戴好,便赶紧出门敲了敲安平继的房门。
如果孙玅音的信被孙耀拿走了的话,那么孙玅音怕是凶多吉少。
想到这里,姜慈更用力地敲了敲,不出一盏茶的功夫,只见安平继已然穿戴好衣服,将门打开,一脸茫然地看着她,“今天又不看诊,我睡到这个时辰不算过分吧?”
姜慈根本懒得理会他,只揪着他的衣领说道:“我说要看诊那就要看诊,你赶紧给我去。”
安平继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他不住地摸了摸头,“姜慈,之前不是说好了我治我的病,你查你的案,咱俩互不干涉吗?怎么你这是出尔反尔啊?更何况,你银子还没给我结,我那终疾谷有大大小小一百二十九个师弟们要养活……”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姜慈不耐烦地将他用劲从房里拽出,厉声道:“你再给我啰嗦一句,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你那终疾谷一百二十九个师兄弟。”
安平继怕了。他虽然知道姜慈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出身皇宫,见多了这些手段,狠起来自然是不在话下,更何况她还有一个暗卫统领大人做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