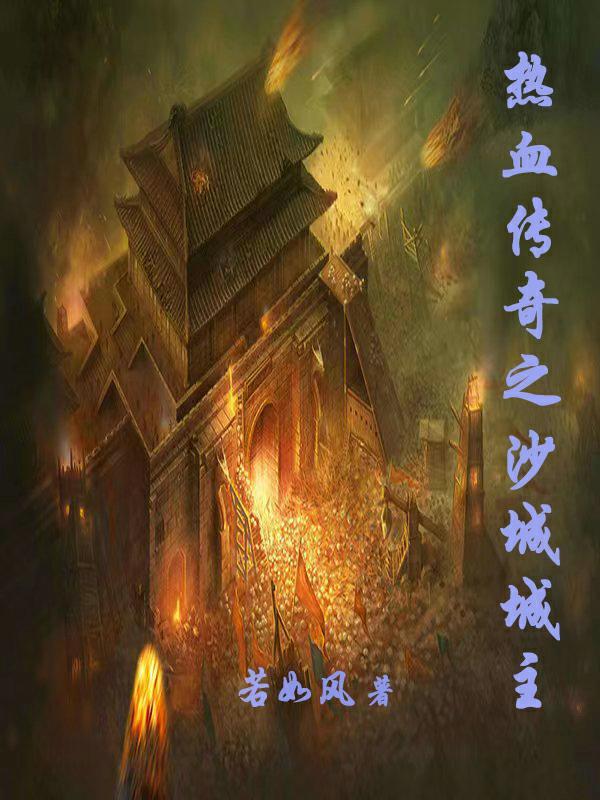69书吧>病弱皇太子by潇潇风声 > 第133章(第1页)
第133章(第1页)
裴珩冷声道:“便让他来,当场拿住,省得叫他跑了。”
赵诠领命去了,裴珩坐起身,拿了兵力部署图细看,见萧知遇有些忧色,笑道:“不必担忧,也只威远军棘手些。前些年我将威远军分作东西两营,西营算是宋玄升麾下,这关头他心里有数。”
萧知遇道:“那淮安王……”
“淮安王记恨于我,他外甥在威远军中任职,怕是没少在长定侯耳边煽风点火。”
一提起淮安王,裴珩便想起萧宥,只觉拔舌都不解恨,牙根发痒,“也好,一并除去了事。”
萧知遇听他这般平静,才安心些。
待到五更时,殿外传来簌簌的响声,萧知遇听得出那是箭羽声,他甚至瞧见许多支箭刺破窗纸,猛然钉在列代先帝的供桌上,灵位哗啦倒下一片,可称是大不敬。
外面虽是刀兵声不断,叱骂声叫喊声响成一片,萧知遇屏息辨认许久,却并未听见萧容深的声音。他知道以容深的性子,定然还在外藏着,不肯轻易出面,随时准备倒戈逃离。
他想了想,朝裴珩低声道:“太医给你用的药还有么?”
兴庆宫内两方打作一团,宫外,萧容深远远立在阴影里,泛着血丝的眼睛紧盯着殿门,不肯放过丝毫异常。
他带来的这一支禁军还算骁勇,不过片刻便分了胜负——裴珩意外重伤暗逃至此,所带的亲卫想来不多,明显抵挡不住,只得退入殿门死守。
萧容深低喝道:“包围兴庆宫,莫让他们逃出去!”
胜券在握,他心中还隐隐有两分不安。萧氏这一代都亲眼见识过裴珩的厉害,对裴珩忌惮犹深,即便胜利在望,他仍有疑心,吩咐不许轻举妄动。
然而这伙禁军是朔州的势力,俱有自家的王侯主子,对萧容深这无权无势的颇有看轻,眼下形势分明要胜了,加官进爵指日可待,怎能不兴奋忘形。很快便有胆大的禁军不听号令,持刀奔近院子,忽而鼻尖一嗅,激动地喊道:“药味,好重的药味!皇帝怕是要不行了!”
此言一出,在场的均是蠢蠢欲动。萧容深闻言亦是心头一震,一种即将迎来命运转机的狂喜将他淹没。
他已枯等四年,生擒新帝改朝换代的天大功劳,甚至是登临帝位的绝佳时机,他怎能放过!
萧容深再不犹疑,当即抽刀,率众策马奔入宫门。
他一入宫门,兴庆宫的守卫像是终于得到了一个信号,藏在石柱后和屋檐上的众多亲卫随即现身动手,赵诠大喝道:“尔等胆敢谋逆,抄家灭族之罪!”
萧容深哪还顾得了什么罪,一路纵马奔向紧闭的殿门,也不管马蹄冲撞践踏的是自己人还是敌方,满心只盼能得头筹。殿门窗纸俱被鲜血染红,不知是裴珩的,还是侍卫受伤所留,浓重的血腥气混着药味令他血脉偾张。
两方禁卫军厮杀混乱之中,他刚踏上台阶,忽听一阵尖锐的破空声,一道飞箭凌空疾射而来。
他猛然间身中一箭,砰地摔下马,滚落台阶,犹有剧痛与愕然。
只见殿门一开,竟有数十亲卫冲出来,裴珩正坐在堂内,脸色虽苍白,却仍是神情冷凝,缓缓放下一张轻弓——他竟还能开得了弓。
眼看自己这一方逐渐不敌,明显是进了圈套,萧容深面如死灰,心知大势已去。若非裴珩受了伤,只怕他在进了宫门那一刻,裴珩的箭就已到眼前了。
他被侍卫押在阶下,还有心求得生机,极力仰起头,眼珠直往屋内瞧,果然就见萧知遇立在近旁。他便怀着几分侥幸,面露恳求,嘶声道:“二哥!容深求你……”
萧知遇没有反应,裴珩却冷冷打断道:“朕还不知你竟如此看重兄弟情分,这关头了还要叙旧。”
他说着,嘴角露出个冷笑:“正巧,恭王也念旧情,屡次向朕和先帝上奏,要请你去他那封地做客,一尽地主之谊。如此,不日便可启程了。”
萧容深脸色猛然惨白下去。
恭王正是远在南边的萧宜明。
他知道萧宜明多次讨要他,不是为了什么兄弟之谊,恐怕是为了报复。
待到天明时,京师内外胜负已分,南衙禁军严整,宋玄升又率部分西营威远军与老父对峙,终于将宋老侯爷劝降。宋侯爷被削了爵位,念在大半辈子的军功,流放北疆,罪不及家人。
这桩大案牵连甚广,除了昭斓郡主一家,庆王萧时丰与英王萧岁和这两个无辜稚童,及几个依附的小宗不曾参与,其余朔州宗室株连泰半,在朝中势力也顺势根除。连那淮安王也革了王位,贬为庶人。
唯有萧宜明远在南边封地,多年来老老实实从未有异动,逃过一劫。
裴珩倚在榻上,仔细将案卷奏章看了,萧知遇在旁替他写朱批,看到萧宜明的封号,翻开奏折一瞧,上面是来迟的恭贺新帝登位之语。言辞简短,大约并不是十分服气,也还算恭敬得体,奏折末尾,问淑太妃安。
萧知遇知道宜明未曾掺和朔州宗室这些事,一是因无能为力,二也因母亲至今还在宫中——先帝为拿捏萧宜明,直接驳了他迎生母去封地的奏折,封为太妃在宫中安享晚年。
想到淑妃,萧知遇心里叹息,轻声道:“听宫人所说,淑太妃这些年郁郁寡欢,既然大局已定,不如送太妃去和宜明母子团聚。”
裴珩拿了奏章一看,道:“你不记恨?”
“该还回去的都还了,太妃是良善之人。”
萧知遇想起从前宜明没少得罪裴珩,便又补充道,“宜明年少时作的孽多了,还是看你的意思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