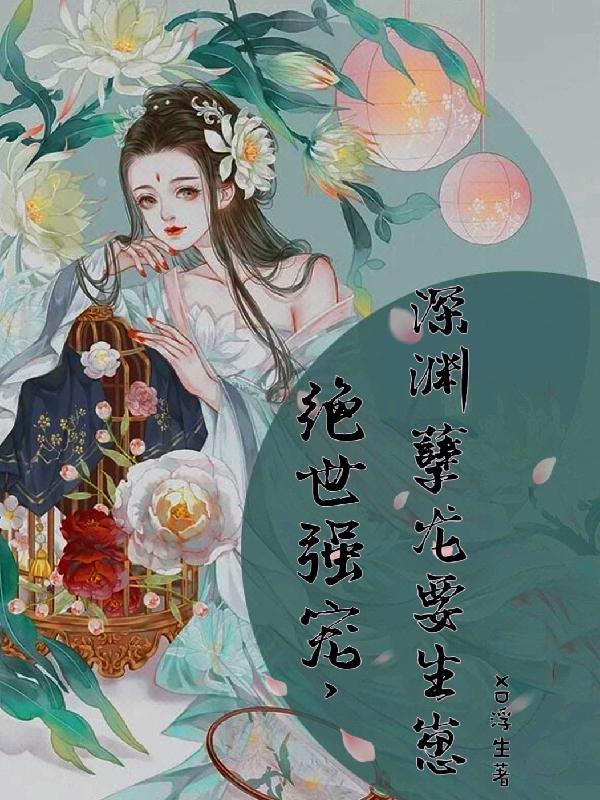69书吧>徐梁国个人简介 > 第147章 红颜(第1页)
第147章 红颜(第1页)
“三郎不在长安,你若一个人在府里无聊,就回侯府去住好了。”
郑太后抱着手炉,坐在池边观鱼,身边跪侍着几名女子,一人抱着一卷书,等着讲经。
“那可不行,传出去都说母亲溺爱我了。”
明容笑了笑,将绒毯又往上拉了一下,斜倚着靠枕,往池子里撒了一把鱼食。
“少来,吾什么都依着你,你还担心这些。”
她扭头对一名女子说道,“今日不必给吾讲了,昭阳县主就在此,有何见解,都说与她听。”
一听是昭阳县主,那几名女子立刻眼睛一亮,为一人兴奋道:“妾素来听说县主的名声,百闻不如一见,今日一观,果然神采飞扬,乃女中豪杰。”
明容嘴角噙笑,把装着鱼食的钵放在山迎手里,坐正了些,想了想又靠回去,“先把书放下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今天不谈书,来谈英雄如何?”
“英雄?你这孩子又憋着什么坏呢?”
郑太后笑道。
明容低下头抿嘴道:“母亲,我与她们说英雄,也是在给您解闷,怎么反而不领情呢?”
“好好好。”
郑太后莞尔,向那几名女子招手,“你们别拘着了,想你们从前在家里时,也不似这么正襟危坐,且靠过来,年纪还比昭阳小呢,坐得跟木头似的,瞧她,往那儿一瘫下就没个正型了。”
几个姑娘憋着笑,膝行而前,朝郑太后靠得近了些,明容抓了一把干果扔到几人怀里,姑娘们手忙脚乱兜住,又笑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明容问为那人。
“回县主,妾名柳年,郑州人氏,年十三。”
柳年一双杏眼,美目流盼,小圆脸尖下巴,行坐间娉婷袅娜,也是个美人胚子。
“柳年,你来说,论英雄,你先想到谁?”
柳年微微蹙眉,思考片刻,果断道:“论当世之英雄,自然以忠勇侯徐公为先。”
“你倒是嘴甜。”
嘴上这么说,明容确是很受用,又问道,“为什么是忠勇侯呢?”
“忠勇侯屡屡自风云际会之时匡扶社稷,救大梁与黎民于水火,忠勇无双,有不世之功,若论北扫突厥,饮马瀚海,亦与大汉长平侯、冠军侯可并提。”
“照你这么说,长平侯、冠军侯,也是英雄。”
柳年颔道:“妾每读到冠军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语,都觉荡气回肠,满腔热血,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也。”
明容点点头,又问旁边一名鹅蛋脸、丹凤眼的姑娘:“你呢,你又怎么说?”
“妾、妾姓何,行七,论英雄,妾想,当有屈子。屈子,惊才风逸,壮志烟高。以身殉国,其仁义之至,令妾钦佩。”
“何七娘,你的名是什么?”
何七娘愣了愣,腼腆道:“回县主,妾名七娘,没有什么正经名字,让县主笑话了。”
“以后要做女官的,没有名字怎么行呢。不如我替你向太后求个恩典。母亲,她以后也是要侍奉您的女官,为她赐名可好?”
明容问道。
“妾卑贱,怎、怎能烦劳太后娘娘!”
何七娘吓得匍匐在地,磕头请罪。
郑太后莞尔,让宫女拉住她:“你奉吾为主,吾赐名与你,算不得什么。”
郑太后垂眸想了想,道:“折若木以拂日兮……吾本期你如兰草,可倒不如树木坚韧,以神木名你,若木,望你守得住。”
“多谢娘娘、若木多谢娘娘!”
待这几人一一说完,明容才喝了口茶,起身踱了几步,转过来道:“听你们都头头是道,可见不说学富五车,也是读过不少经史子集,虽都论古今列侯才子,却未必不知道商之妇好,汉之孝烈将军,又至谯国夫人、平阳昭公主,言语中却未曾提及,何故?”
“并非你们的过错,无非英雄往往只赋予男子,非得到女人身上,也要先说巾帼不让须眉,添个‘女’字叫女英雄。否则……论今朝,我也该称英雄是不是?”
她狡黠地向郑太后眨了眨眼,郑太后无奈地笑道:“还说你不贫嘴了吾不习惯,果然还是憋不住!”
“母亲选你们进宫,并非只为了你们去伺候后宫里的嫔妃,那些活儿,随便哪个宫女都会,不必读书。而论说做女官,后宫亦有六尚局,要你们何用?难道你们不曾好奇吗?文臣武将,有人论政三省,有人管辖江河漕运,有人戍边征战,有人抚恤万民,这样的好差事,是没有俸禄,还是遭人唾骂,为什么没有女官做?”
“这……”
几名女子面面相觑,越听越觉得惶恐,跪坐着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不敢接话。
“这些事情,或许我不能实现,你们也不能实现,可是再下一代,下下代,乃至千代、万代。”
江山可十几代易主,可是女人诞育世间千万年,不低头,总有成的一天。
待那些女子退下后,郑太后屏退众人,拉着明容在池边,搂着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