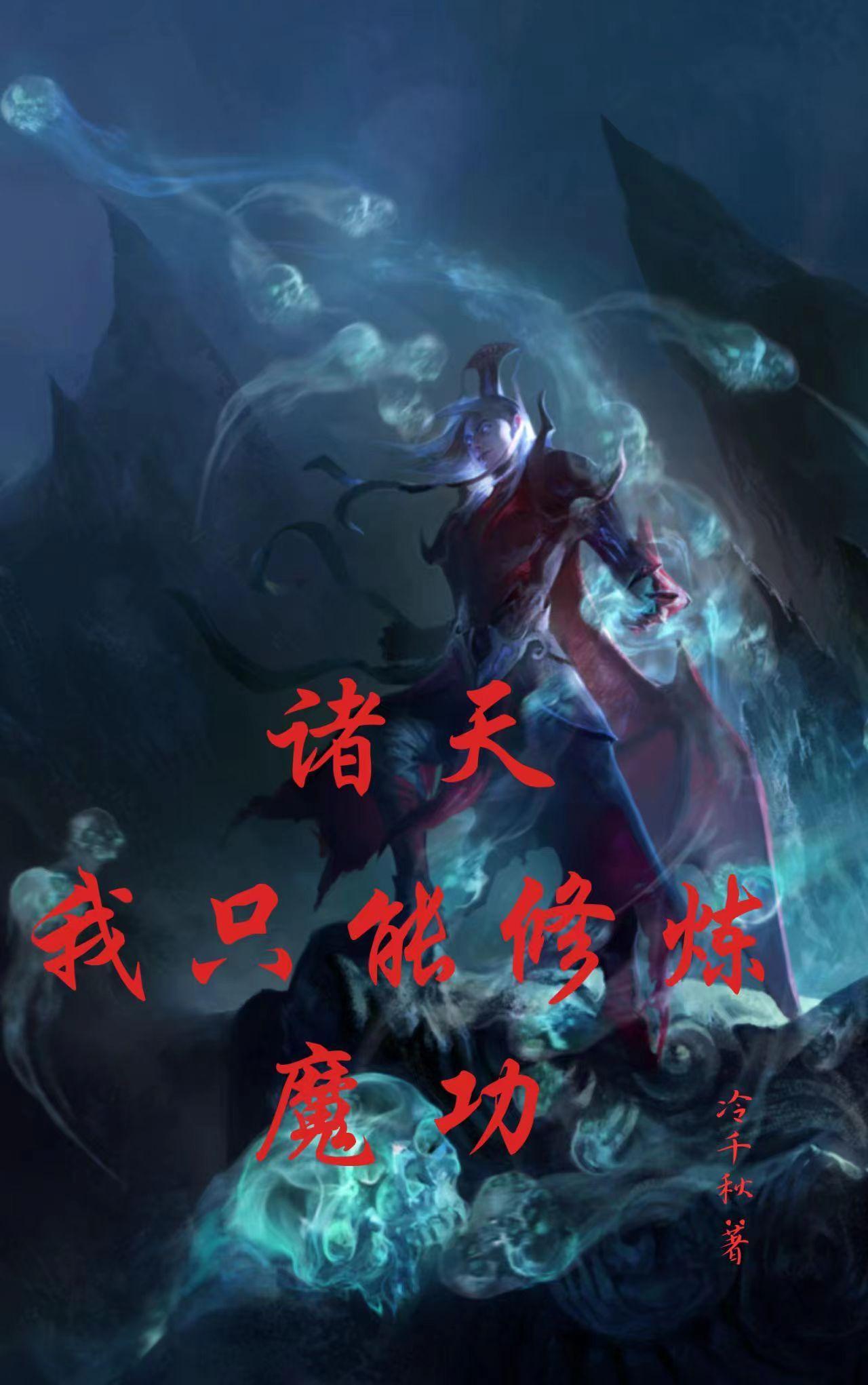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请渉给我 > 加更(第1页)
加更(第1页)
宴绥目光落在她腿间的稠液上,感受着她蜜穴轻微的颤抖,眼眸里带笑的狡黠涌动着。
“不要?”
余非的抵抗的姿势就如同笑话一样,宴绥轻易地就能将她拉近顶弄,让她在自己身下溃不成军。
他拍了拍余非的臀,在感受到穴肉的猛绞后,嗤笑着,漆黑深邃的眼眸带着嘲弄的笑意,他抬起余非的腰,低沉的声音在深夜里宛若鬼魅:“现在说太晚了吧?”
粗长的阴茎高频率地在花径内抽动。
宴绥伸手揉捏着白嫩的乳肉,熟练地顶胯,以睥睨的姿态去望余非迷离恍惚的眼神。
他感受到余非的甬道急促地收缩起来,胡乱地搐动,绞得他皱眉,嘴角却微微上扬带着笑意。
理智仿佛在快感中湮灭,余非抓住他的手臂,哭喊着弓起腿,试图逃离下身侵袭的快感:“关伏…”
起先还笑容满面的宴绥身影一顿,握着她乳肉的力度也重了几分。
“我是谁?”
余非还未从高潮里回过神,她呜咽着挺着腰承受小穴痉挛的欢愉,没有发现自己说了什么,视线不再清明,关伏的身影与宴绥不断重迭:“关伏,抱抱我…”
“你真的是…”
宴绥望着她,轻笑出声。
可他的心,仿佛在一点一点地冷下去,沉入深不见底的冰川水里。
他手上的力度愈发重了,捏得余非疼得喊出了声,宴绥才反应过来,松开手,冷冷地看着她。
眉骨仿佛载着连绵的雨一样湿冷。
他还没说什么,便见余非捂住双眼哭了起来。
原来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欢愉哭的。
是讨厌他啊。
宴绥早就停下了抽插的动作,面无表情地拭去她的泪水:“和我偷情委屈你了?”
“你问过我愿意吗?”
余非哭着去推开他,却被宴绥死死按住。
她想逃,宴绥便偏偏按着她,将她往自己身下靠去,让他们交接的部位紧紧地交缠,严丝合缝。
“是不愿意和我做,还是除了我,谁都可以?”
宴绥想起来余非今天和裴或跳舞的那幕,怒火中烧,太阳穴也有些发涨地痛,手也气得有些发抖。
看着多般配啊。
偏偏余非也同样被他的话气红了双眼:“除了你,都可以。”
宴绥气昏了头,他捏住余非的下颚,逼迫她视线里只可以有自己:“余非,你听着。”
“你的这些话,伤不了我,也赶不走我。”
他摩挲着余非的脸颊,看着缠绕在他食指上的碎发,缓声道:“你最好明白一件事。”
“我不在乎,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不说结束,我们这段关系就结束不了。”
亏他费尽心机过来找她,结果人家根本不想见到他。
本来今天一天的心情都不好。
此刻宴绥更加感觉自己就是最大的一个笑话。
他抽出水亮的阴茎,皱着眉帮余非绑好浴袍,随后走近浴室拿纸随便擦了擦仍然勃起的阴茎。
出来时,床上的人已经无影无踪。
他穿戴好衣服,正好望见那走下二楼慌乱去寻关伏身影的余非,抿唇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