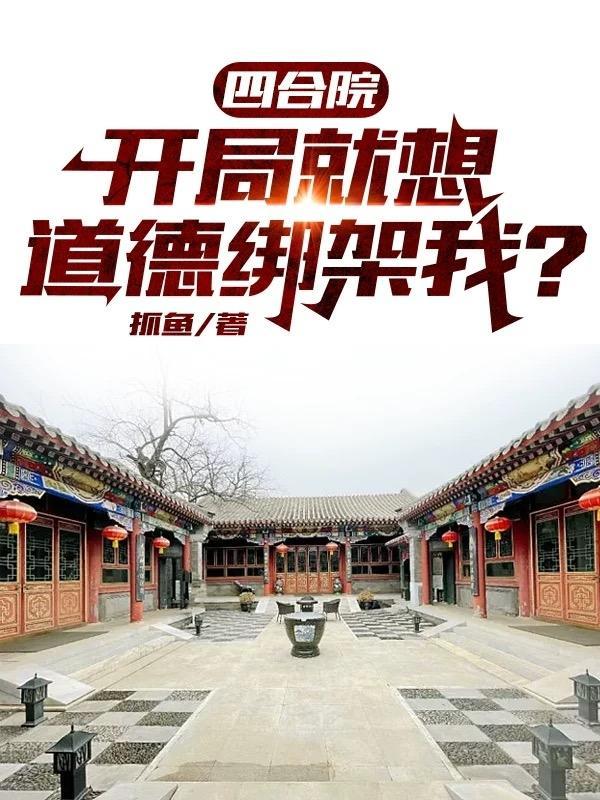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福寿咸臻是什么意思 > 第28章 箜篌引(第2页)
第28章 箜篌引(第2页)
皇后斜着一双碧睛,轻轻捻着海棠花瓣,笑道:“这是苏轼的诗,皇上深为喜欢。”
宁嫔温和含笑,挑着一弯明月秀眉,笑道:“主儿得圣眷,连这等乐事都熟知于心,奴才拜服。”
恭常在娇柔浅笑,道:“奴才见主儿亲自教授太子读书识字,饮汤喂药,事必亲躬,真是辛苦。”
皇后笑意温柔,随手扯了一枝海棠花,道:“太子将来要践祚大统,岂敢有一丝懈怠?恭常在无子,日后有了孩子,便能知晓吾的一片苦心了。”
恭常在依依施礼,莞尔不言,宁嫔的妆色沉静如水,不见一丝波澜,道:“这几日瑞悆微微咳嗽是不是偶感热寒?奴才炖了一壶枇杷膏,劳烦皇后主儿替奴才喂上几口。”
皇后心中阴沉,却见翠雯横眉冷对,道:“宁主儿是信不过皇后主儿伺候,还是信不过奴才们伺候?你的五皇子调教得千伶百俐,且玉澜堂什么东西没有,还缺你一壶枇杷膏么?”
6忠海抬眼一笑,道:“皇后主儿贵为中宫,轻易不抚养嫔妃之子,宁主儿知足吧。”
宁嫔脸上挂不住愧色,嘴上却是不输,道:“可奴才毕竟是五皇子生母,奴才为五皇子熬一壶药都不许么?”
皇后含着婉顺的笑容,道:“你炖的枇杷膏,吾会喂给瑞悆饮下,你有这般口舌,倒不如回了阁,好好瞧一瞧书,再不然为皇上添一添皇子。”
宁嫔眉头一皱,花枝轻摇,忙恬静优雅的抿下了嘴角的阴沉,道:“嗻,奴才数日见不到瑞悆,实在爱子情深。”
王嬷嬷不觉冷冷剜了一眼,道:“皇后主儿是嫡母!难道会委屈了你的孩子?”
宁嫔立时变色,冷艳一怒,却见恭常在紧紧拉住她的衣袖,摇头皱眉。宁嫔闭目须臾,踟蹰不定,恭常在忙换了和悦容色,道:“嬷嬷说笑了,五皇子得皇后主儿悉心教养,宁嫔十分感念主儿恩德。”
皇后抚着耳边的三钳东珠坠,笑靥渐渐清冷,道:“你是吾抬举过的人,一言一行上些身份,别像畅音阁的婢子一样,失了规矩。”
宁嫔眉梢带笑,微微颔,盈盈施了一礼,她望着皇后、王嬷嬷离去的背影,唇边凝了一缕狠辣。
这一日午后,丽嫔怀抱四皇子从煦贵人处回来,却见万寿山的乱柳杂花,垂杨藤蔓之后隐约闪过一阵青翠色的衣衫影子,不过须臾,又见大皇子匆忙路过,神色不安,极为惊惶。
丽嫔心下狐疑,便驻足凝眉,低呼道:“是谁?”
苓桂眉头紧锁,贴过丽嫔耳畔,道:“像是玞贵人与大皇子,听说玞贵人会弹箜篌,有一次亲得了大皇子排曲。”
丽嫔轻扬眉黛,嘴角涌出一丝冷笑,道:“是么?玞贵人身为皇上嫔妾,倒也不避嫌。”
章廷海嘴角凝了暗沉之色,道:“玞主儿年轻,且是乌拉那拉氏出身,势必与主儿一争高下。”
丽嫔咬了咬唇,便扬起一双妙眸,道:“小小妮子她也配!”
章廷海垂声道:“她是不配!可是皇后主儿提拔,主儿若不趁早除了这个祸患,想来忧愁无尽。”
丽嫔脸上波澜不现,却暗暗沉下脸来凝神闭目,道:“仔细留意着玞贵人、大皇子。”
章廷海阴暗着脸忙点了头,而丽嫔却笑意盈盈,眉目濯濯,如清冷明月的一树春柳依依,清娟动人。
到了下午,慧妃、荣嫔、嫤常在笑意盈盈坐在亭子中,六月的昆明湖畔一池碧莹莹的绿水,夹岸桃花轻绽,绿柳如荫,郁郁芳芳,湖上绽放着株株荷花,朵朵袅娜,田田荷叶,从湖上吹过的微风习习,轻巧徐徐,有着荷叶菱香的独特韵味渲染了盛夏的宁静。
亭子一畔种植着牡丹、芍药、藤蔓个个花开缤纷,圆硕艳丽,经夏日的暖风轻吹,只觉衣衫留香,轻盈拂过犹有丝丝芬芳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