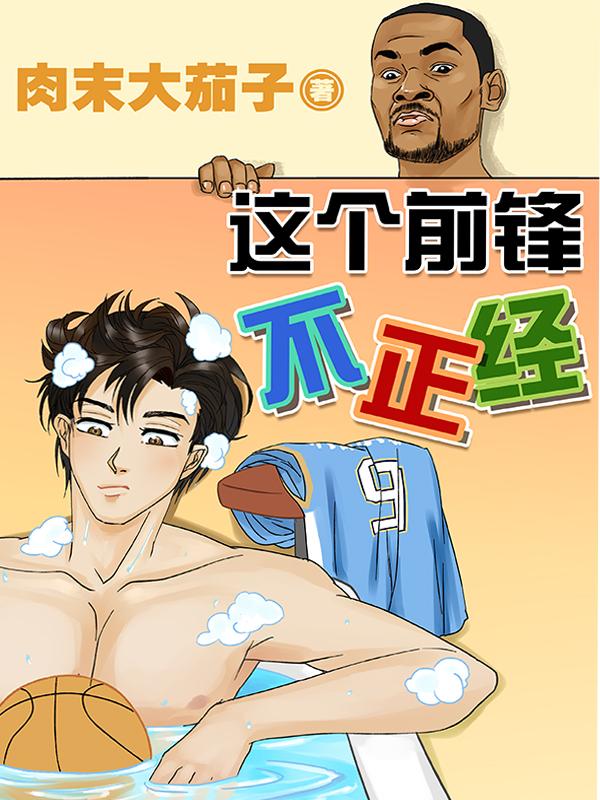69书吧>折刃怎么画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夏天的庆州很凉快,营中空地燃着驱蚊的草药,薄雾绵绵,散发着宜人的清香。远处四散着守夜的将士,其余人大都睡下,兰烽帐前无人,他亦没有多想。
营帐里还是会有些闷热,天上繁星点点,他几下脱掉外袍和长靴,赤膊上身,一手提着袍子,一手掀开厚重的帐帘。
这营帐中仅住他一人,地方还算宽敞,摆着一张行军床,地上铺了薄绒毯,还放着简单的案几。
兰烽掀开帐帘的手顿了一瞬,看着帐内的场景,心跳都漏了半拍,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他立刻用力放下,阔步走入营帐内。
福嘉穿着男伶统一的灰麻布短衫,足踩一双黑布鞋,一头乌发在头顶梳成一个髻,她坐在兰烽那张小床上,眸子亮晶晶的,优哉吃着一颗硕大的枣干。
她听见动静,刚要同兰烽打招呼,却见进来的人露着精壮的上身,看到她时,脸上有一瞬的空白,样子还蛮好笑的。
福嘉暗叹这身段着实好,冲他一笑:“好久不见。”
兰烽诧异地看着她,也顾不得更多,拎着外袍上前将她兜头盖起来。他确认四下无人,才沉声恼道:“你来做什么?不要命了?”
天气热,兰烽穿这件外袍没衬中衣,贴身穿的。袍子裹住福嘉的脸,带着淡淡的汗味,却不难闻。
她扒开袍子,只漏出一对眼眸,看着对方,心中暗叹这身段着实诱人:“不会有危险,我看过了,你这营帐位置最好,周围铜墙铁壁。”
兰烽声音不自觉颤抖,两地相隔数百里,福嘉怎么来的,路并不好走,水路险厄,陆路颠簸,方才在外面也没有看见车辇。
他跪在床边,双手紧紧握住她胳膊:“别拿自己开玩笑,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福嘉费力地从身后挪出那把旧手刀:“你是不是没带刀,我怕你用别的不称手,给你送来了。”
她看着兰烽紧绷的薄唇,路上想出逗弄他的话都说不出口了。
他怎么这么凶巴巴?
这个理由不能说服兰烽,他的刀有什么要紧?若她说来看太子,甚至来看曹暄鹤,都可信得多。
庆州并不安全,东胡人若是拼尽全力,日便能兵临城下,虽然关上城门,也能守个三年五载,但那日子并不好过。
他看着福嘉轻松的神态,显然没把危险放在眼里,她大概是觉得好玩,或者像和大皇子争斗时一样,完全没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眼里。
兰烽克制着情绪,沉声道:“收拾下东西,我现在就送你回西京。”
留宿
福嘉来的时候倒也没想着久住,她凭一股执念,吃了不少苦头赶来,也就是想确认兰烽安全,再把刀送过来,了却一头念想。
但是兰烽这凶狠模样,让她感情上不大能接受。
她有些逆反:“我刚来怎么就要走,总要先歇歇的。”
踢掉鞋袜,她干脆一副今晚就睡这里的态度,盘腿在小床上歇下。
兰烽心急如焚,没有妥协的余地:“不行。”
他带上一队人,趁着夜色走,不会被人发现,消息若是传出去,路上恐有人蓄意劫持。
福嘉还要说什么,兰烽没给她机会,抱住她就要起身。
福嘉挣扎起来,可是她哪有什么力气,被对方一只胳膊就扛到肩膀上。肩膀硌得慌,她奋力拍打兰烽的后背,蹬着腿要下来,后背上肌肉紧绷,她拍得手生疼,足尖划在他腰间的匕首上,顿时一道血痕。
福嘉疼得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不要走!”
兰烽听她声音不对,才将她放下来查看,白生生的脚背上一道红痕,刮掉一层油皮,好在没出血。
兰烽清醒过来,自责道:“对不起……”
福嘉在气头上,根本不搭理他,抬起小腿踢在他胸膛上,撇着脸不说话。
兰烽握住那只擦破皮的脚,心疼地从床下翻出伤药,雪白的小瓷瓶,还是福嘉上一回给她置办的。
福嘉用力动了动,没能将腿抽出来,细嫩的脚腕握在他粗粝的手掌中有些痒,她看他小心抖了药粉上去,又要去寻纱布。
“没必要,”
福嘉气鼓鼓地:“你这个人真讨厌,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兰烽垂着眼,也不愿同她对视,点头道:“嗯。”
福嘉一双脚踩在他膝盖上,右脚踝系着红绳,上坠一枚金色哑铃铛,随着主人的动作轻轻摇摆。
兰烽安静下来,才觉得不自在,那道朱红色刺目,让他脑中闪过两人中蛊时纠缠的画面,福嘉抹胸系带,细细搭在她肩膀上,被动作弄得有些松散。
兰烽闭了闭眼,赶紧转移注意力:“是臣的不对,殿下来一定是有要事。”
福嘉听得稍微顺耳,别扭开口道:“我舅舅最后一次出征,就是没带刀,我那天收拾你的东西,发现你也没带。”
她委屈地说:“我心里有这个坎,总觉得不吉利。”
兰烽没想到,她真的是为了送这把刀来的,他解释:“你送我新的,我自然带着你送的。”
他看着福嘉认真又憋屈的表情,不敢再与这双明眸相对,视线落在那把刀上,眼前一热。
一把便宜的手刀,一条贱命的他,他何德何能?
福嘉皱起鼻子,看他脸上变化:“你哭什么?你倒委屈上了?”
她收回脚,哼了一声:“说不定我救了你一命么,也不晓得感谢救命恩人。”
话音未落,她便落入一个宽阔的怀抱。福嘉好久没有因为被抱而被抱住了,他是慢慢拢过来,像是在给她反悔的时间。
兰烽先是同她贴近,用胳膊慢慢包住她的肩头和后背,接着不断收紧,一点点挤压掉他们之间多余的空气。被温暖的身体包裹其中,福嘉感受着对方皮肤轻微的战栗,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