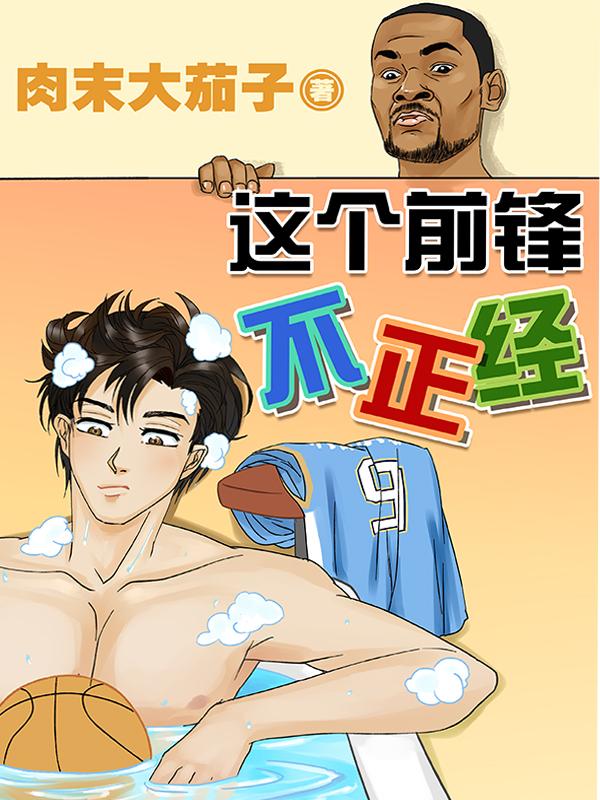69书吧>贺新朝 txt > 第7节(第2页)
第7节(第2页)
纪榛触及那双不再带有笑意的桃花眼,明知强求只会让沈雁清厌恶他,却还是不懂得悬崖勒马。
心心念念的人近在咫尺,他情不自禁伸手去抓沈雁清的衣袍。指尖方碰到柔软的衣角,沈雁清便往后退了一步,眼中有不解、亦有冷嘲。
纪榛失望地收回手,垂着脑袋,羞赧着支吾道:“那日你送我的花我差工匠涂了油,可存百年不腐。。。。。”
“什么花?”
纪榛心口一颤,懵懵地看着沈雁清。
沈雁清眉头紧锁,似对他所说之事毫无印象。
原来在他看来弥足珍贵的相遇,沈雁清转眼就忘却。
见纪榛缄口结舌,沈雁清冷声说:“事到如今,我已无意探究你何时对我起意。你父兄多番胁迫我与家人,我才勉为其难来见你,如今你我见面,不如把话说个明白。”
“我平生最不喜依附家族而活之人,你纪榛家世再显贵,容貌再上乘,情之一字,皆由本心,强人所难只会适得其反。”
纪榛本就苍白的脸色又煞白一分。
“趁事未成定局,莫要再执迷不悟。”
纪榛何尝不知道沈雁清言之有理,但正如对方所说,“情之一字,皆由本心”
,他心之所向是沈雁清,如何叫他剖心剔情,舍情弃意?
他见不得沈雁清与他人成亲生子,白头偕老。
就当他执而不化。
纪榛沉默半晌,抬起红透的眼睛,“若我非要一意孤行呢?”
沈雁清劝慰无果,神色冷若霜雪地丢给他四个字,“冥顽不灵。”
这之后到成婚近半月的时间,纪榛再没有见到沈雁清,但每日都在期盼着新婚之日。
期间发生了一件让纪榛亡魂丧胆之事。
他不顾兄长的阻挠外出亲自置办龙凤镯,岂知当马车行至人烟稀少的街道,竟有一支长箭直直射入他的马车之中。
长箭擦过纪榛的耳边,带起的风声震如响雷。
只差一寸,锐利的箭头就该射穿他的脑袋,让他命丧当场。
他不知这是意外还是有人刻意为之,但婚娶之前最怕有变故,纪榛不敢将此事告知兄长,亦扼令吉安守口如瓶。吉安原是不肯,耐不住纪榛一再哭求,这才替他瞒了下来。
纪榛毫发无损,却惊吓过度因此病了两日,烧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兄长纪决当他着凉,衣不解带地照料陪伴他,他才有所好转。
成婚后不到三月,吉安在向纪决汇报之时说漏嘴,这才将长街一事言明。
纪决大发雷霆,将纪榛痛斥一顿。纪榛卖乖讨饶多日兄长才肯搭理他。
如今纪榛再回想起来,也许那支长箭意在提醒他渎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既然他现在能好端端地活着,想必连上天也在怜悯他一颗痴心。
月色被乌云遮盖,纪榛辗转难眠,顾不得会被沈雁清嘲讽,一个翻身起塌出门。
他只着中衣,顺着走廊微弱的灯笼光摸到东厢房,轻轻抬手一推,门咯吱开了。
沈雁清竟然忘记落锁。
纪榛喜不自胜,溜进去将门关好,又摸着黑蹑手蹑脚来到床前。不等沈雁清赶他,连忙掀开被子钻进被窝里抱住那截劲瘦的腰身。
他没少做这样的事,动作行云流水。
沈雁清似早料到他会来,语气淡淡,“扰人清梦。”
纪榛抱着人不肯撒手,脸颊在沈雁清颈处蹭着,因为害羞,声音黏糊糊的,“沈雁清,我睡不着。”
对方投怀送抱的意图太明显,沈雁清却坐怀不乱,甚至拨开那只在他腰间乱动的手,“可我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