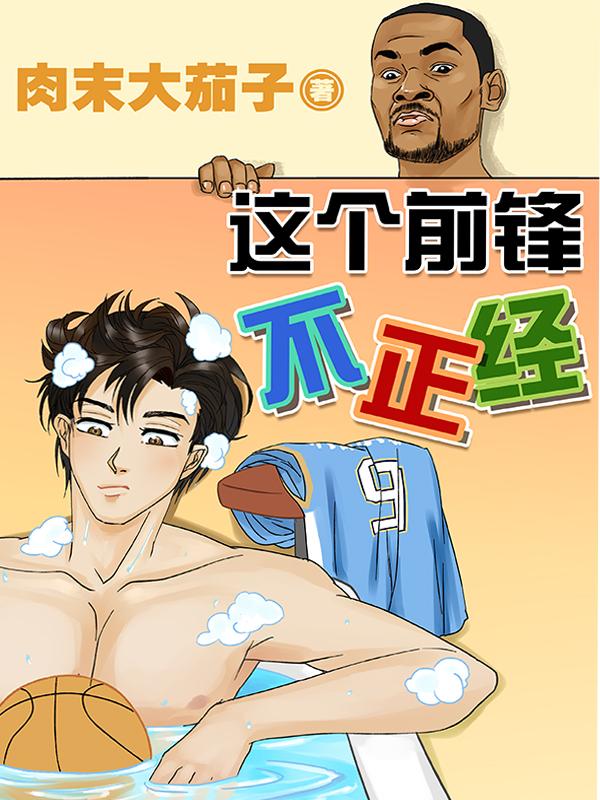69书吧>歪打正着免费完整版 > 第5章 风雨同舟5(第1页)
第5章 风雨同舟5(第1页)
当我们与大部队会合的时候,已经是几天后。
看着迎上来的营副教导员,好像没有想象那么热烈。
一直以来,我认为的会师,哪怕像电视剧里万里长征后的吴起镇会师,都是那种拼命的奔跑,然后热烈的拥抱,激动的表扬,或者是挥舞着红旗在一起。
而那天,只是一个军礼,一个握手而已。
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
他带着一营的炮连和机枪连随着团主力到了这里,已经建立起了营地。
直升机空投了物资,营地上炊烟四起,我们迫不及待的等着干饭,所有的人都饥肠辘辘。
但是看着白副教导员的表情,很沉重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事情一样。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我们团在这次抢险中出现的第一个伤亡,巴朵班长,牺牲了。
在来的途中,为了给一处被困的村民送药,团长让它游了过去,但是没能再游回来。
我们甚至都不能去找它的遗体。
估计未来在下游,无论谁能看到他,都会以为是一只普通淹死的狗子,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条军犬,因为它实在没有军犬的样子。
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与它斗智斗勇的样子,这只老狗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我心里在咒骂团长,抢险救灾,你带着它干嘛?
它是自己跳上车的!
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所有人都陷入了悲痛中。
更要命的是,我还出现了恐惧。
这种恐惧与誓言无关,与其说之前的信誓旦旦,或者说这几天的遭遇与豪言壮语,都没有让我意识到我将面临着什么?
那句烈士陵园见,我们当时说的很轻松,可是现在现这不仅是沉重,更多的是恐惧,害怕,或者说想临阵脱逃。
现实面前,赤裸裸的骨感,我就是怕了,虽然没有尿裤子,但是心里抖的厉害。
我为有这种想法而羞耻,但是管不住自己的腿在“攥”
筋。
我看到的一片汪洋,是一望无际的,泼天的汪洋,那个水库不是什么风光秀丽的,举目之内,已经是到处泽国,6地少,水面多。
湖的正面已不再是碧水蓝天,什么青山环绕,全都没了昔日的样子。现在有的是黄色的、满是泥沙,一浪又一浪的拍着大堤的洪水。
大堤好像在天天颤抖。
太吓人了,这与之前遇到的小堤小坝比,不可同日而语。
天空不停的在响着炸雷,闪电有的时候像是把天劈开了一样,长长的,把天空撕成布条,四分五裂的。
大堤上迎面的风,平日里都在三五级之上。
暴风雨说来就来,夜里一点多,大风夹着暴雨扑打着大堤,迎头的大浪把人打的头都抬不起来,眼睛根本睁不开。
谁也没有想到真到了这里,情况会是这样,我们全是新兵,傻傻的跟着老兵和干部们,连排长们大喊着口号带着头往堤上冲锋。
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了任何的军人自豪感,只是想回家。
我突然又想起来以前说的那句话——好铁不打钉也许是对的,面对接二连三的七八米的大浪,自己就是来送死的。
人,太渺小了。
我不敢往前冲,甚至还想往后退,直到刀疤从后面踹了我一脚,才回过神来。
“快去烧水”
他说,不能让战士们冻着,他们得喝热水。
“是”
我还是在傻站着
“你他妈的的在干什么,快”
刀疤刚刚骂完,就听到有人喊:“那边出口子了”
说着他顺着来人指的方向看去,无数的战友没了命的从大坝下方扛着沙袋往上冲,上面有百十个兄弟不停的往口子里投石子扔沙袋;
水要漫过子堤,那就有危险,必需继续加厚,加厚,再加厚,然后让上游的三营想办法继续找地方泄洪。
团长在电话里拼了命的骂“三营长,报告位置,报告位置,找到泄洪点,给老子炸了。什么?没炸药了?直升机上不来?那就派人运,想尽一切办法,就是用手抠也得泄洪,保持太阳湖水位,这儿要是溃了,下游就完了”
这边,有几处水冲破了子堤,水流太急,沙袋根本不好用,而用来堵口子的笼子又太重。
熊四海他们这时派上了用场,之前人家一个人一个沙袋,他四个,两个肩膀,前后各搭一个,冲的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