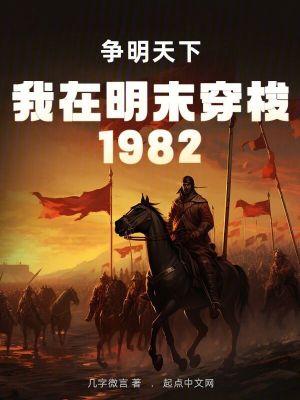69书吧>子骗世家有声在线收听 > 第24章 寻旧情北上哈尔滨3(第1页)
第24章 寻旧情北上哈尔滨3(第1页)
琪友年轻气盛,能喝几口,陪着甄永信喝了几杯。
吃过饭,女主人收拾了碗筷,三个男人又回正厅喝茶,谈论一番世仁的去处,到底没谈出个头绪,便又闲扯了些别的事。
琪友像他父亲一样健谈,只是还年轻,略显冒失,不如他父亲说话那么中听,却能讲出一些大实话,加上长相和世仁有些像,虽说初次面,甄永信却觉得亲性。
“在铁路上搬运,累吗?”
甄永信问道。
“咋不累呢?随便叫出一件东西,都是二百多斤,一天车上车下的几百趟,歇工的时候,浑身都快瘫了。”
琪友抱怨道。
“那就换个工作呗。这扛苦力的活儿,终不是长久的事。”
甄永信说道。
“刚下学时,有人介绍我到小学教书,”
琪友心怀怨气地说道,“可我爹愣是不让,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非逼我到火车站去。
“年轻力壮的,吃点苦,多攒点钱,免得老了吃苦头。”
宁凤奎替自己辩解道,“眼下是累些,好在年轻人,能扛得住,等到我和你姑父这个岁数,想去挣钱,都不行啦。”
“哼,多挣钱有什么用?”
琪友嘟囔道,“钱到了你手里,还不都得输光?”
“这孩子,咋越说越走样儿?”
宁凤奎嗔斥儿子道,“我还不是想去赚点外快,为了你和你妈?”
“外财不富穷命人。”
话不投机,琪友扔下一句,起身回屋睡觉去了。
甄永信听出,琪友这是对父亲嗜赌不满。
果然,宁凤奎有些吃不住劲,胀着脸嗔斥起儿子。
在厨房洗碗的妻子听见,奔了过来,到正屋门口,见屋里只是丈夫一人在说,便忍住了气,没有作,狠瞅了丈夫一眼,转身回了厨房。宁凤奎见妻子拿眼狠瞪他,也把握火候,停下声来。
甄永信就此判断出宁凤奎在家中的地位。
“琪友一天能赚多少钱?”
甄永信问道。
“活儿好的时候,一天下来,总能赚个三十五十的。”
宁凤奎说。
甄永信听过,兀然想起自己年轻时走背运时,到老毛子的铁路工地当劳工的事,心里滋生出对琪友的同情。
想到自己现在腰间带的黄货,琪友即使不吃不喝,恐怕一辈子都赚不到,便有了要帮帮这年轻人的想法,借机对宁凤奎说,“哥,我看琪友这孩子有文化,又机灵,天天到车站去出苦力,是屈了孩子。你看这样成不成?我现在到处寻找世仁,也需要一个帮手,让琪友来做我的帮手,一个月我给他三十块大洋,保准比当苦力挣得多,也累不着孩子。”
宁凤奎听了,眼里放出光来,毕竟也是一把年纪了,见过一些世面,还能装出稳沉,一板一眼地说道,“这样一来,好是好,早年我也听来凤说过,你们甄家是金宁府的富室。只是平时也没什么事,每个月就拿这么多钱,这不等于白白让你赏琪友钱吗?说出去,也是好说不好听呀。”
甄永信知道宁凤奎又把这事和他跟宁氏的关系扯在了一起,赶忙辩解道,“哥想错了,我这次到各地走走,一来是找世仁,二来也是跑生意的,要是有合适的生意,也需要琪帮着做呢。等将来有了大生意,赚得多了,我还要和琪友平分呢,恐怕一个月就不止几十块大洋了。”
“这个,我得和你嫂子商量商量。”
说完,起身去了厨房。
半袋烟功夫,两口子回到了正厅,一进门,女主就“咯咯”
笑着,满口都是过年的话,“你就说嘛,他姑夫,今儿个一大早呀,我一睁开眼,你猜怎么着?就看见头上悬着一个红喜蛛子,知道咱家今天要有喜事了。你瞧,这喜事真的说来就来了。你说灵验不灵验?”
说了又笑,边笑边去喊琪友来,把好事告诉了儿子。
琪友得知了消息,也忘记了刚才和父亲怄气的事,兴冲冲跑过来问道,“姑父要带我做什么事?我能行吗?”
“你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