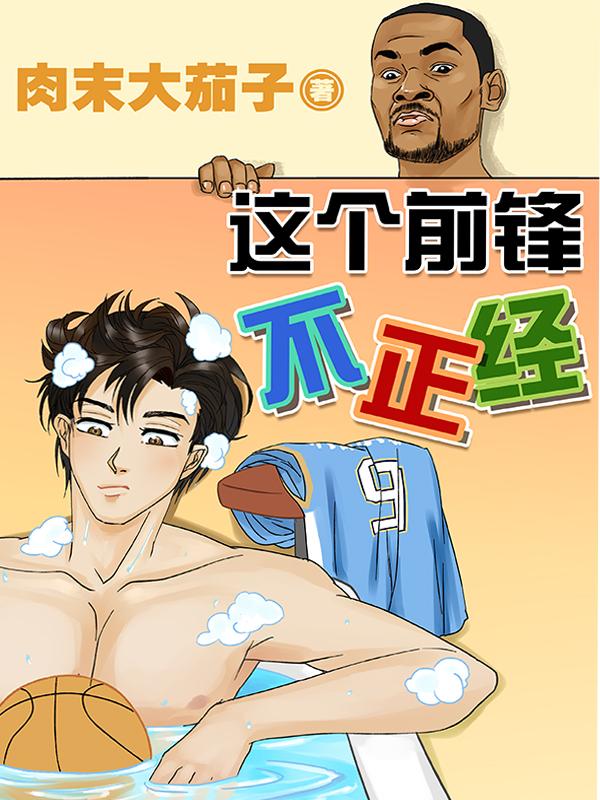69书吧>我和老攻的恋爱的恋爱循环快穿全文免费 > 第9页(第1页)
第9页(第1页)
阮墨停下动作,“我…借一件衣服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麻烦么,恪非没有说话,关灯拖鞋跟着躺在床上,面无表情地用被子把他给包成一个球。
两人陷入沉默,阮墨被带着他体温的被子裹着,心像是被柔软的针扎了一下,有些酸胀的难受。
“恪非。”
他的声音很轻,还带着一丝颤抖,“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恪非闭着的眼睛动了动,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太难,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想通。
或者说,他不敢想通。
少年抓着被子边缘,从被子球里露出脑袋,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他,带着一点莫名的期待。
黑暗里,恪非严肃的脸开始慢慢烧红,可他太黑阮墨又近视,谁也看不清谁,最后只得到他一巴掌按在阮墨头顶,把他彻底拍进被子里,裹得严实合缝。
恪非:“废话那么多,睡觉。”
……
恪非又做了那个困扰他多年的梦。
梦里,父亲穿着一身少将的军装,把年幼的他直接带进了特种兵部队,跟着一群被国-家领养的孤儿特训。
白天训练,晚上就跟着父亲回家,和温雅的母亲一同吃饭。
一家三口平凡幸福地过了十几年。
直到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带着一等功的奖章,把他童年的一切完全推翻。
他和母亲大吵一架。
他要去从军,战场是他的归宿。可她不同意,强硬地从军营搬走,把他送进a市高中,想让他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
梦境的最后,恪非惊醒,额头一层浅浅的汗。
窗外是黎明前夕最黑暗的时候,冬季的清晨五点,天际不见一点光亮,暗得仿佛一块冷硬的砚。
一个温热的手臂横在他前胸,他的单人床虽然宽大,但与两人来说还是有些拥挤,睡相不雅的阮墨早就热的挣脱了被子,把旁边的他当成人形抱枕,一边抱着还嫌弃的撇嘴,似乎是嫌这个抱枕实在太硬。
恪非拿开这条不安分的手臂,又被更紧地抱回去,手脚并用仿佛八爪鱼。
“别跑…小兔兔……”
他呢喃不清地低语,带着懒洋洋的困意,吹在恪非颈间,让他呼吸一窒。
恪非对他的好感度开始上起下浮,7o,8o动个不停,波动了接近一分钟,最终才逐渐稳定,一点一点退回5o整。
视线太差,恪非看不清他的模样,小心伸手摸上他的顶,顺着他侧脸的轮廓向下描绘,动作不轻不重,是少见的温柔。
从额角到鼻尖,再到总是胆怯抿着的浅色唇瓣。
恪非的动作停住了,呼吸稍稍加快了度。窗外亮起一点晨光,叫他看清了少年薄唇轻启,浅浅呼吸的样子。
着了魔一般,恪非的目光越来越沉,靠近再靠近,一寸一寸挨着他的鼻尖,吻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