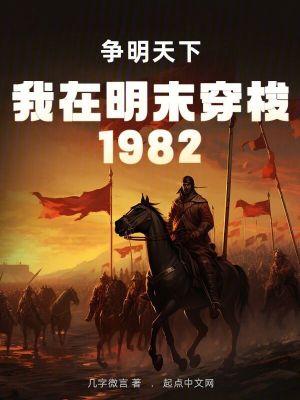69书吧>狐狸小夫郎的报恩番外 > 第4页(第1页)
第4页(第1页)
胡吱恨恨地磨牙,好个刁钻自闭的人类。他紧了紧单薄的粗麻衣,在桌上躺下,缩成一团。早晚,早晚床是他的,软绵绵的褥子也是他的!
-
热烈的日光从破碎的屋顶和漏风的窗户,大大咧咧地照耀。
胡吱睁开眼,泛着泪花,打了个哈欠。他第一眼便去找司空,现人不在床上,顿时紧张起来,怕人跑了。打开屋门,入眼是空旷的院子,点缀着几株浅紫粉红的野花。
整片院子的蒿草被清理干净,整整齐齐地摞在院落的一角,唯独野花安然俏丽,保留着春天的情。
塌了一半的土灶已经重泥好,甚至因为司空带的锅子比较小,被改小一圈,重适应了铁锅的尺寸。灶台一旁,捡拾的一摞干柴,整齐排列。
司空正蹲在灶台下,不时添些柴火。
炊烟袅袅从灶台升起,胡吱嗅到了清的香气。司空这家伙,动身能力也忒强了些,一大早,饭都做好了。
胡吱凑到他旁边,好奇地问道:“司空,你在做什么好吃的?蛮好闻的。”
司空抬眸,清瘦的面颊沾染了一片灰迹,配上他那张面无表情的冷脸,莫名搞笑。胡吱不客气地笑出声,伸手便要抹去痕迹,被他敏锐地躲开。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知被嫌弃了多少次的胡吱恼怒异常,直接上手,双手捧住司空的脸,上下揉搓,任他左晃又晃,无法挣脱。
火光的照耀下,司空的耳尖偷偷染上了红色。
他从未和人这么亲近过,被人捧着脸磋磨,更是平生第一回,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很是不自在,害怕地连连后退,一屁股蹲坐在地上。整个人笼罩在胡吱的阴影下。
胡吱居高临下,鼓着脸问道:“我有那么吓人吗?”
司空揉了揉被搓红的脸,缓声说:“倒也不是。我只是不喜与人亲近。”
一与人对视,就会紧张,一与人靠近,就莫名的恐慌。他天性如此,本就打算分家后,自己一人过。
他做了十九年的傻子,一朝灵台清明,再看过往就好似蒙了一层纱布,朦朦胧胧,不似自己的故事。
父母健在时,很疼爱他,穿衣吃饭都是家里顶好的一份。父母不断叮嘱大哥二哥,要疼爱自己这个弟弟。
实际上呢,父母去世后,在司大哥家里的五年,他过得并不好,住在猪圈旁搭的小棚子里,一日三餐不得上桌,只能蹲在一旁吃糟糠剩菜剩饭,辱骂更是家常便饭。
两位哥哥的逢场作戏,父母去世前后强烈的生活反差,按理说司空该是十分悲伤愤恨,伤父母早逝,未能尽孝道,愤哥哥冷漠,兄弟至亲如此不堪。
清醒后的司空回想起这一切,内心竟不生波澜。过往是一出戏,他不过是个看戏人,甚至是一个十分冷漠、难以入戏的看戏人。
司空只想着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过日子。他从善如流地答应分家,打算走过仪式后,便和哥儿说清楚。他现在一穷二白,养不起哥儿,也不想人打扰。
司空不知道为何自己这么封闭,脑海中模模糊糊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和任何人有纠缠,独自过完此生,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人生。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打算践行下去。
只是……司空无奈地看一眼胡吱,这个小哥儿似乎不准备这么轻易放过自己。
胡吱不满地‘哼’一声:“谁乐意和你亲近?不要脸,呸!要不是你救……算了……给你个傻子也说不明白。”
“我不是傻子。”
司空反驳道。
“和你这怪人也说不清楚。这样吧,你给我说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听过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
胡吱想了想,说道。
司空把心愿说给自己听,简单的小愿望,比如想要换个大房子,有良田十亩之类的,百分百祈愿成功。若是大愿望,比如位极人臣或者家缠万贯,实现的几率能提升个四五成。
胡吱想着如果司空说得是大愿望,他可能需要花些时间,从中助力。小愿望听完就可以实现,完成报恩,修仙去。
胡吱说得没头没脑,司空满脸疑惑。说出愿望,决定要不要离开?难道是想看看自己这个郎君有没有志气,上不上进?那可太简单了,他的毕生心愿就是无人打扰,混吃等死。
“哎呀,你怎么不说啊?想不想换个和你家大哥一样的大房子,或者有几亩良田,从而吃喝不愁?”
胡吱引导着对方,想让司空的愿望小一点,好快点离开。
司空认真地回道:“我想你离我远一点。”
好聒噪,心慌。
“你!”
胡吱刚要说话,突然有人喊道:“哟~这是来的司空小夫妻吗?”
篱笆墙不遮人,刘大婶一眼就能望见两人,瞧着一人叉腰站着,一人坐在地上,像是吵架,赶忙出声打断。
司空迅低头,往灶台内添柴火,整个人写着四个大字——“看不见我”
。
有人来,胡吱不得不招呼,离开他身旁。应验得还真快。胡吱吐槽一句,出了大门,笑容满面打招呼:“正是呢。大婶知道我家相公?”
“叫我刘婶就行,我就住旁边。司家做这等缺德事,村上人谁不知道呢。”
刘婶迅瞥了眼自我隐形的司空,怜悯地看着胡吱:“瞧你多俊俏的小哥儿,嫁给……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你刘婶,邻里邻居的,彼此有个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