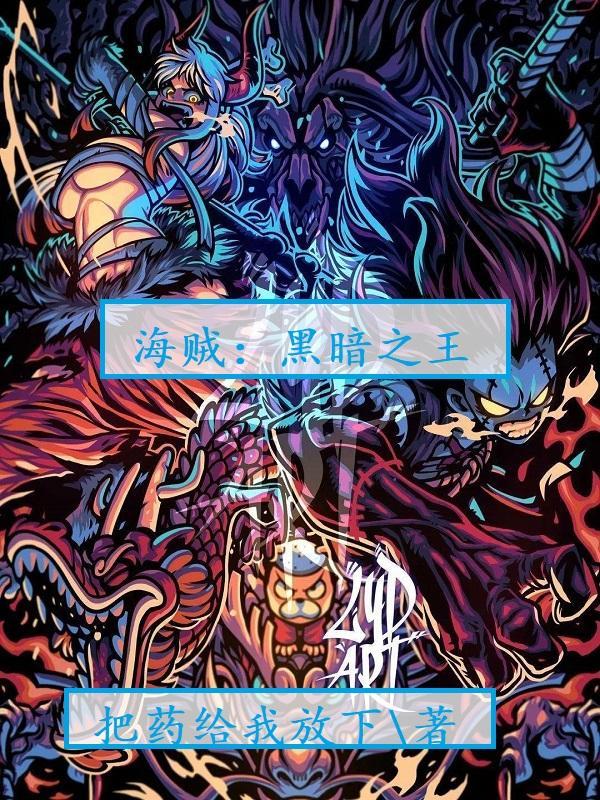69书吧>朝夕光辉 > 第27章 悍妇遭屈辱上(第1页)
第27章 悍妇遭屈辱上(第1页)
人心隔肚皮,谁人可从第一眼便瞧出其真伪?话说何重越在山间茅屋遇着的几个贼人来路他已猜出几分,若非意外。
点破也无甚好处,此番邀约石任意远去采买字画便是他想出来的奸谋,不置石任意死地,也要让让石任意备受折磨,无非是令石顶富知晓而悲痛无奈。
恩恩怨怨,世间几人能放下?何重越决计放不下,他打路过椒城,与石任意互换信物,见着红玉之后再也无心只顾四处从商,他要替父亲报仇的念想便一日高过一日。
山林重归静寂,何重越也该离开,月余时日,在此养伤,今日离开,心中多少有些不舍。
轻移脚步,四处瞧瞧,莫说在此养伤,哪怕在此长居也令人惬意。屋中、院中一草一木都让人喜爱。
褡裢就在肩头,他与石任意约好在山下相见,一道就去金陵。深吸一口气,徐徐吐出,不再回头,锁了门,出了院。
山下村人来来去去,虽然稀疏。眼前,从未失约的石任意正与一村人悄语。慢慢走近,近至二人身旁。
石任意瞧见了他“贤弟来了。”
“嗯!”
有些好奇,随口便问。“石兄,你们在说些什么?”
“没甚。”
石任意略忖量后道:“方才这位大叔说近来县城出了一桩奇事,有一女子死后复生,还说去阴司走了一趟,贤弟你说这事可信否?”
人死复生?何重越怕是不信,他若信了,他父亲含恨而死,他岂能袖手一旁,不设法救活父亲了?
“哦?这倒新鲜,石兄,你觉着如何?”
石任意略叹了口气。“我不好说信或是不信,随他去吧!贤弟,我好不容易说服家父,就说要去金陵求见一位昔日朋侪,因着他的才学远在我之上,却两次秋闱名落孙山,倒要问问其中可有关窍,以作防备,父亲这才允准。赶路吧!”
“哈哈,记得石兄说过厌恶为官,愚弟才一门心思教你营商之法,兄莫不是惦念不下,这会真的又有了为官的心思?”
“唉!父命难违,秋闱试他一试,成败我都不挂心上。”
面色坦然,毫无遮掩。
从他说话的口气可评断,石任意真个无心为官。
“这便好,石兄有仙风道骨之姿,他日必能得偿所愿。哈哈哈!”
何重越亦知石任意有脱凡之心,奈何天下哪有什么神仙,至少,何重越绝不相信神灵存在世间。
“贤弟说笑了!”
石任意接话,而后便紧了紧自个肩头的褡裢,他先个迈步。
随他一道,前处便有马车相送,他们这会将途径县城,而后再去金陵。
……
“我说你那孽子只怕死性不改,此番出门并非去会朋侪,而是另有所图啊!”
孙桂花冷语道。
石顶富岂会不疑?但他又能怎样?孙桂花与石任意虽已几分和缓,但日积月累的厌秽如何容易化解?从孙桂花口中说出的话已够石顶富心烦,因着孙桂花并不知晓,数日之前,石顶富花了银子想要在山林茅屋之中了结了何重越的性命,怎奈那何重越果真有些能耐,五个受雇之人竟不敌一个年岁轻轻的小辈。
意图瞒天过海,瞅准了自个儿子---石任意也在茅屋的时日,欲图将自个置身事外以蒙骗何重越,留一手防备蹉败,哪知就真个杀不了何重越,即使五人确实未道出幕后真凶,石顶富仍心神不宁,估摸着何重越大体也猜出了些。
“桂花,为夫打算出门一趟,你自个好生留在家中照看。”
一横眉,冷眸瞧来。“夫君不是挣了那许多银子了吗?何故又要出去?”
“嗯……我……我还想再挣些钱财归来,秋闱将近,里里外外繁费不能少。”
“夫君,你我八年夫妻了吧?”
略蹙眉头,石顶富道:“是啊!八年了,桂花为了这个家操持,功不可没,为夫不会忘记你的好。”
孙桂花摇摇头,冷笑一声。“哼哼!夫君过誉了,桂花哪有甚么功劳,倒是不能为你生儿育女,算是愧对了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