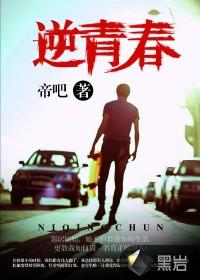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穷时候 姜淑梅简介 > 第56页(第1页)
第56页(第1页)
百时屯的人知道娘回家了,都来看她。原来的床给送回来,支上了。锅碗盆勺油盐米面,也齐了。
不断有人来问:“还缺啥?”
娘哭了,再多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中了,中了。”
大伙儿送的粮食还没吃完,姜庄齐的粮食送来了。姜庄离百时屯三十里路,住的都是姓姜的,跟俺们是一家子。他们推来五个木头轱辘车,一个车上装两布袋粮,十布袋就是一千二百多斤,有高粱,有黄豆。过年的时候,邻居送来的东西更全科,猪肉、牛肉、羊肉、小鸡、白面、胡萝卜、大萝卜、白菜、粉条,啥都有。
那时家里九口人,三哥十七,俺十二,小妹十岁,饭量都大。过完春节,送来的粮食越吃越少,眼看就断顿了,大哥愁得睡不着觉,眼睛熬得通红。他跟三哥商量,想借钱买个弹棉花机器,俺那儿叫“洋弓”
。三哥去城里仁大娘家借了钱,买了洋弓,拉到仁大娘家。第二天,仁大娘起早给三哥做饭,他拉了四十五里地,中午到家了。
大哥说:“士彦,我去刘庄找个人安装吧。”
三哥把脸一沉,说:“你去呗。”
大哥看三哥不愿意了,不再说啥,也没去刘庄。三哥吃完午饭,不大会儿就把机器安装好了。他拿出家里的棉花试,邻居看棉花弹得好,都往这儿送。弹到天黑,换了三十多斤粮食。三哥长这么大没出过力,这天拉车走了四十五里路,回来又蹬一下午洋弓,晚上连说话的劲都没了。
娘心疼,说:“士彦,歇两天再干吧。”
三哥一天都没歇。蹬洋弓是个力气活儿,蹬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三哥天天都挣来一百多斤粮食。
吃喝不愁了,余下的粮食卖了,把钱还上。俺家又买一个挤棉花籽的轧车,当时叫“洋轧车”
。干一天能挣一百五十斤棉花籽,俺家再把棉花籽卖给油坊。手里宽绰了,家里换上驴拉的洋弓弹棉花。开始一个毛驴拉,看一个毛驴拉太累了,又买了一个毛驴。两个毛驴拉一天,能挣二百多斤粮食。
四外庄上没有洋弓、洋轧车,都到俺家排队。看俺挣钱了,百时屯又有两家买洋弓、洋轧车。大哥和三哥一商量,把挤棉花籽的洋轧车卖了,还卖了一个小毛驴。钱够了,就开起药铺。那时候有句话,“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都不热”
,说的是这两个生意最赚钱。
二哥以前有个朋友叫张学奎,五十多岁,住在独山黄村,是个有名的大夫。他儿子也是大夫,家里也开药铺。大哥到独山把他请来,在俺家药铺坐堂。
张先生在百时屯看病,看得可响了,百时屯人送他外号“活神仙”
,找他看病的排队,远道的就在俺家住下。张先生在药铺坐堂三四年,分文不取,还手把手教大哥学看病。
他跟娘说:“俺不缺钱,俺是来帮你的。”
五月节、八月节他都不回家,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娘心里过意不去,一直让张先生吃小灶。
药铺生意好,大哥和三哥根本忙不过来。冬闲的时候,曹海的两个表弟过来帮忙,他们也啥都不要。汤药价钱贵,张先生就给病人开药丸,药丸便宜,效果还挺好。药碾子叮当一响,俺就知道,他们又干活儿了,中药压成药面后,再打成药丸,他们四个人经常忙到半夜。
家里留下的洋弓和小毛驴都交给小妹了,两个人的活儿她一个人干。她还练出一个本事,棉花用手一提,就知道几斤几两,一点儿不会差。俺在家纺棉织布做针线活儿,两个嫂子磨面做饭织布纺棉。家里马上要起来,来了运动。
这次运动叫社会主义改造,俺家的药铺变成“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药铺归了公家,大哥留在药铺当大夫,按月拿工资。百时屯连着两年遭水灾,没了棉花,洋弓也没用了。为养家糊口,三哥跑到吉林,出了两年苦力。
婆家的家史
婆家祖上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北老张庄,爷公公叫张善奎,为人忠厚老实,他给张春桥家做长工。张春桥他爹张开益,看爷公公是个可靠的人,就在龙固集南买了五十多亩洼地叫他种,给他牛和车,还给他盖了房子,说是收了粮食一家一半儿。人家从来不问粮食收了多少,送多少收多少,人家是想帮他。
刚到徐庄,爷公公挨欺负,后来听说地是张开益的,就没人欺负他了。
爷公公有七个孩子,三个闺女四个儿子。大姑长得好,聪明伶俐,跟本屯子的一个男孩私奔了。后来大姑叫人传信,想回来看看爹娘,爷公公嫌她丢人,到死也没让大姑进门。
二姑也聪明,身材好,干啥啥行,就是一脸黑麻子,出天花落下的。她在婆家挨打受气,肋巴骨断了一根也不知道,她总说肚子疼,婆家也不给看,说死了更好。
爷公公带着二姑去看病,先生也看不出是啥病,就给开了两服汤药,吃了好一点儿,不吃药还是疼,二姑瘦得皮包骨,脸焦黄。结婚第二年,她生个女孩,叫松。要是生个男孩,她的日子还能好过些,生女孩是赔钱货,她就更难了。
二姑父娶个丑媳妇,心里总不舒服,天长日久心里不痛快就有病了。他多次要休了二姑,他娘不干,他娘说儿子:“人家又没做错事,你有啥理由休人家?老话说,休了前妻没饭吃。
老话还说,娶媳妇不讲丑和俊,把家做活值千金。”
他娘不叫儿子休媳妇,儿子窝囊,病死了,松才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