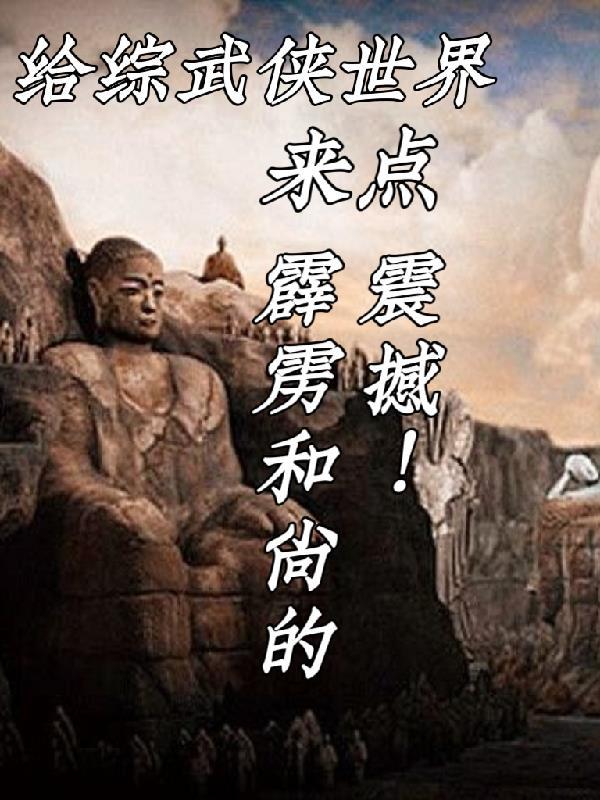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举起女巫的锤子免费 > 第97页(第1页)
第97页(第1页)
“别怕,艾玛,”
克莉斯安抚道:“有个教会派来的刺客想杀我,已经被我杀死了,他们并没有要毒死我……”
但艾玛只是看着她摇头,深陷的眼窝中露出惊惧。
克莉斯忽然明白了,“曾经有人对我投毒,对不对?是……我们在王宫的时候?”
艾玛瑟瑟抖,显然这件事对于她有着很深的印象,让她一直陷在恐惧中无法自拔。
“他们……是谁?”
克莉斯问道。
“我不知道,”
艾玛的眼中闪过茫然,“巨大的影子,无处不在,他们要你死,小姐,他们反对你继承王位,他们影响国王,让他冷待你、厌恶你、驱逐你,他们说你的母亲是女巫,然后逼死了她。”
克莉斯遇到的刺客来自教会,这几乎确定无疑,但克莉斯没想到刺客的袭击却引动了艾玛的记忆,让她误以为这个刺客来自于阴谋诡谲的马灵宫廷——很显然在马灵的宫廷里,原主遭遇过一次类似的袭击,有人对她投毒,但毒死了一名侍女。
现在她又听到了这个讯息,宫廷有一股巨大的势力盘踞其上,但关键是这势力是针对她的,是反对她的。
而且他们将这种反对付之行动,贯彻到底——甚至逼死了原主的母亲,曼涅夫人。
在这一刻侍女艾玛的行为终于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她要杀死一同从王宫出来的侍女玛莎,因为玛莎很有可能就是那股反对势力派来的卧底,静悄悄潜伏在克莉斯身边,等待从马灵来的指示,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告女主人为女巫,并将之送上火刑柱。
马灵的信件。
原来如此。
克莉斯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身处在危机四伏之中。
一艘大船,毫无方向,周围是通天彻地的海浪,桅杆下是悬浮的黑影,死猫的魂灵。
海妖饶有兴地从海底窥视着他们,然而它自始至终并没有露出真身,只是通过它令人迷醉的歌声,看着这一艘船上的人在惊恐、畏惧和自我猜忌中沉沦。
“您应该询问她更多,”
克莱尔道:“否则当她清醒的时候,她又要三缄其口了。”
“她认为这是对我的保护,我记得她提起过我以前似乎也失忆过,”
克莉斯从密室中走出来,主仆二人并肩走在空旷的楼上:“我的确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比如我的母亲曼涅夫人。”
“我听说她是有名的美人,”
克莱尔道:“她的美丽一直在欧洲流传。”
“很多人都说过她的美貌,”
克莉斯道:“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的死亡,她像一朵玫瑰,突兀地凋零了,这让我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我本来就为记不起她的容颜而懊恼,然而今天我又被告知,我的母亲很少和我亲近,想想也是,我在彭巴博的乡间住了十一年。”
克莉斯停留在楼的楼梯上,楼梯和所有欧洲城堡一样,墙上挂满了画像。
“彭巴博是我母亲的嫁妆,但那个地方被从地图上抹去,”
克莉斯的目光流连在画像上:“博尼菲是我父亲的封地,然而整座城堡里,并没有一副我母亲的画像。”
但克莉斯又能感觉到这个母亲对她的疏离,也许是一种保护。
“马灵的宫廷在艾玛的记忆中,是个很可怕的地方,”
克莉斯道:“那么让我远离这座宫廷,不闻不问,反而是脱离了是非的漩涡。”
后来克莉斯来到了宫廷,曼涅夫人马不停蹄地给她定了一门婚约。
“在这门婚约中,我是最大的获益方,”
克莉斯道:“我没有丧失继承权,甚至还可以得到一处海港,甚至这个海港上有船只,这些船只在艾玛的口中,可以帮助我逃离欧洲,保全性命。”
楼上停放着康斯坦丁的尸体,一具已经变得青黑色、僵硬如雕塑的尸体。
甚至他的脸上,还保留着面临死亡时候的惊恐和茫然。
他的胸口有个洞,穿透了衣服,血花凝固成黑色的液体,像给他的猎装上蒙上了一层黑纱。
“艾玛说得对,他其实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只是没有很好地约束自己的欲望,”
克莉斯道:“这世上又有几个人能约束自己的欲望呢?”
但克莉斯这仅有的一丝惋惜和愁绪,很快就化作了一种警醒,本该躺在这里的是她,如果她继续还这样庸庸碌碌、懵懵懂懂下去。
“我的敌人有很多,”
克莉斯心道:“在博尼菲,在马灵,甚至还在圣伯多禄。”
克莉斯为他亲手点燃了白蜡,做了诚挚的祈祷,即使并没有履行婚礼,但克莉斯却主动提出来穿上黑纱,这在其他城堡侍女,甚至督西里亚的仆从眼中,这是莫大的哀悼和诚意,他们没有不为克莉斯的举动所感动的——
但在克莉斯看来,她都即将要继承人家的财产和土地了,装也要装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
克莉斯宣告了对督西里亚的继承,她的尖在雪白的信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亲爱的伯父,尊敬的国王陛下,
日安。
您谦卑的、需要仰仗您荣光和恩典的侄女克莉斯,遗憾地告诉您一个消息,我那只见过一次面的未婚夫,督西里亚的康斯坦丁下,在打猎的时候生了意外,丢失了生命以及头上的王冠。
我似乎不幸地成为了一个寡妇,即使这个寡妇从未享受过婚姻的过程,但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母亲,曼涅夫人的心路历程了,悲伤充斥着我的心灵,让我亟盼您的安慰和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