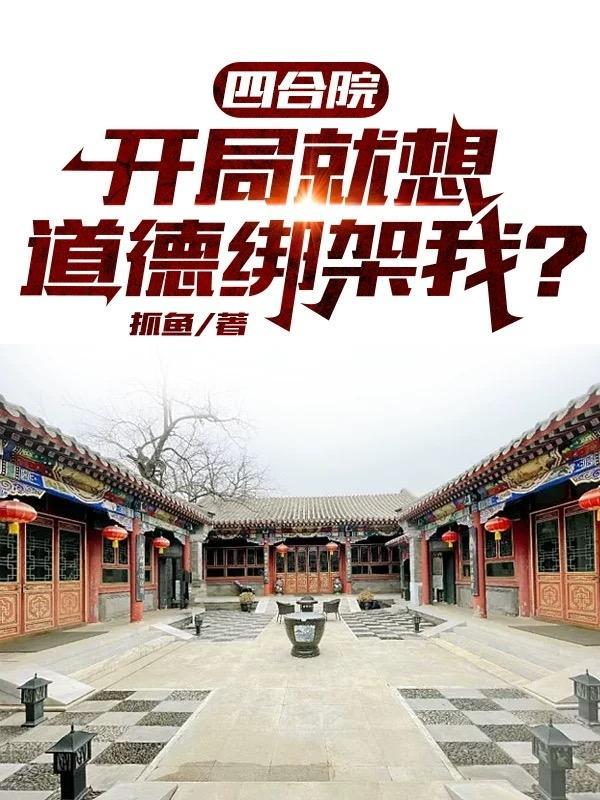69书吧>她日行一善txt全文 > 第50页(第1页)
第50页(第1页)
一连五天如此,陈祺钰再也耐不住了,临睡前敲开了流光的房门:“祖母,孙儿有些事想和你说说。”
流光很累,她已经很久没感觉到这么疲劳了,一日最少五个时辰外输仙力,两颗天精丹给凌骞,两颗自己服用,能保持他情况稳定,离痊愈还早呢。
真仙也顶不住只出不进,人间灵气本就稀薄,她又没有恢复时间,凌骞稳定了,她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打坐,改日。”
小红鸟蹲在她肩膀上内心出奸笑,再折腾她几天,自己一膀子就能扇死她了吧?嘿嘿嘿。
“孙儿一定要说。”
流光撩开眼皮,见他面色凝重,问:“什么事?”
陈祺钰坐到她身边,语重心长:“祖母,您是我祖母,别人可不知道。您这样日日同一个年轻男子共处一室,还不许下人在旁,难免遭人诟病啊。”
流光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仙界混了数十万年,人间历劫九世,她什么都懂,只是往不往心里去又是另一回事了。一听这话她就明白了陈祺钰的来意:“自家府中,遭谁诟病?”
“下人。”
陈祺钰很严肃,“祖母不要小看下人,他们即使卖身于此,亦不能全然相信,素日采买跑腿探亲访友,总会有跟外人接触的机会,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但凡带出一句半句闲话,对您的声名不利。”
见她一脸懒得理会的表情,陈祺钰又压低声音:“有一个人,祖母不知还记不记得。”
“谁?”
“香云。”
当年身边的大丫鬟,跟到渝城后被佟惠容撵回京成亲去了,流光有印象:“她怎么了?”
“这些年,孙儿一直在查一件事,就是皇帝如何得知您未过世,又如何得知您返老还童的。一开始,孙儿怀疑过弟弟们,但试探之后放了心,陈家子孙皆忠孝清正,不负您和祖父的教导养育之恩。而当年知晓些许内情的下人都被孙儿处置了,唯有秦嬷嬷和香云在您力保下得以活命。秦嬷嬷始终跟着您,忠心不容置疑,香云回京之后嫁人,随夫去了京郊庄子,大约三年后,她丈夫病死,成了寡妇,至今还带着一个孩子住在庄上。那个庄子早就换了管事,她娘俩寄人篱下过得并不舒心,可是孙儿派人去问过她两次,要不要回国公府生活,或者可以把她送来渝城,都被她拒绝了。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哪儿知道为什么。流光惫懒地闭着眼睛:“你说。”
“她会不会就是当年泄漏您行踪的人?”
“无凭无据,不要瞎猜。”
陈祺钰冷冷一笑,“孙儿派人盯她好几年,均无异动。可是大前年,她儿子生了重病,她竟拿出了一锭金元宝去请京城杏林圣手,购置许多贵重药材。素日母子俩布衣素食,一不种田二不绣花,全靠国公府每月济些钱财,她哪来的金元宝?”
流光轻哼:“你既怀疑她,为何不把她逮进府去问个清楚?”
“您若不归,孙儿要她一条贱命也难解心忧。虽未动她,但她也跑不掉,她是您的婢子,理应由您处置。”
留着香云,是陈祺钰给自己留的一个希望,他希望祖母回来,能亲口问问香云,当年保你活命,就是给你一个出卖主子的机会?
金元宝也算不上证据,也许人家捡的呢?流光对当年事都不太上心,敷衍道:“到时再说,没事了吧?没事我打坐了。”
陈祺钰见她根本不当回事,急了:“孙儿说香云的事,是想提醒祖母,不要太相信身边人,恶奴欺主不在少数,跨院里每天送饭的,除尘的来来去去,难保不会有人说您和凌骞的闲话。”
“俗话不是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吗?我就是给他治病而已。”
“别人看不见房中景况,又怎知您是在治病?”
凡人破事多,烦死了!流光无奈:“那你说怎么办?”
“房里至少要留两个人。”
“要不明日你来吧,你在房里看着,好不?”
“好!”
陈祺钰一口答应,大大松了口气,“有我在,祖母清誉可保。”
瑞卿在一旁笑得快昏死过去,“嘎嘎嘎,老妖怪还有清誉,九重天谁不知,她人过扒衣,兽过扒皮!”
陈祺钰满意了,临走道:“祖母几时弄了个小玩意儿来养?纯赤的鸟儿少见。”
流光淡笑:“喜欢吗?祖母拔光它的毛,给你煮汤补身子吧。”
想起自己也曾属于被扒的一员,瑞卿情绪急转直下,愤恨且瑟瑟地瞪了流光一眼。
被允许在祖母治病时旁观,陈祺钰只高兴了一晚上,接下来几天都处在更为惴惴的状态中。怪不得不能留人,床上的凌骞衣不蔽体,胸膛下腹皆裸露在外,祖母的手在他身上任意游走,一会儿摸头,一会儿摸胸,在某处停留时间尤其长。。。。。。简直没眼看!
他坐立不安,祖父尊严祖母清誉的严重问题不停折磨着他的孝心,几次想出言制止,不时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但流光功时旁若无人,自动屏蔽外界干扰,任他急出火来也不理会。
前后医治了十天有余,流光倾尽心血耗光仙力,终于补好了凌骞最后一处受损的经脉和脏腑,唯有胸骨裂处还需慢慢静养。她强撑力气回房间,息也不调了,一头栽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瑞卿蹲在床架上看着她无知无觉的样子,瞅瞅四下无人,张嘴对着她吐出一股金色火焰,瞬间燎了流光的一绺头,把方枕烧了个洞。可惜火苗实在有点小,没等烧光她的脑袋就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