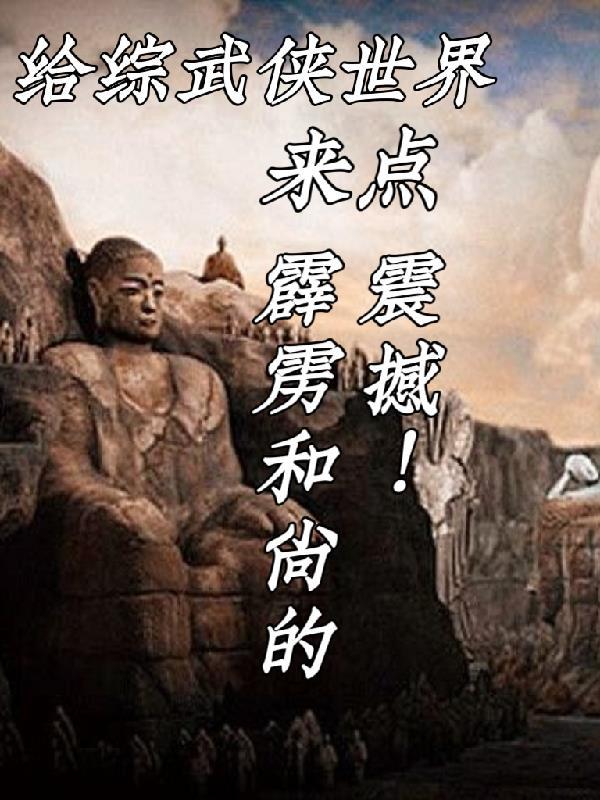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仵作娇娘薄月栖烟全文免费阅读 > 第59节(第1页)
第59节(第1页)
她说完霍危楼却看着她未动,于是她自己伸手拿过他手里的药膏盒子,而后梗着脖子站了起来,见她走出几步,霍危楼也凝眸站起,“你——”
薄若幽见状却肩背微收,似是有些忌怕,霍危楼叹了口气,“这便怕我了?”
薄若幽瘪了瘪嘴,“民女不敢。”
霍危楼指了指榻上,“那你坐下。”
薄若幽有些迟疑,霍危楼便眯着眸子道,“不听话了?”
薄若幽心道最委屈的难道不是她?怎还变成她不听话了?然而敢怒不敢言,只好又回去坐下,霍危楼不由分说拿过药膏,一副一定要给她上药的模样,薄若幽梗着背脊下颌微收的不动,如此,霍危楼自然是没法子上药的。
“侯爷,民女不敢劳烦您……”
霍危楼也不再言语相击,只扯过敞椅大马金刀的坐在她跟前,而后蹙眉盯着她。
二人一时不分地位高低,反倒像她闹了脾气,薄若幽无奈至极,心道尊贵如您何必如此,莫非也心有惭愧,所以才要亲力亲为抵消心底自责?
二人好似对峙一般,偏生霍危楼也不退让,她越发觉得无奈,于是看着霍危楼,将下颌扬了起来,此等模样,倒是不那般令人想入非非,只是她一双眸子瞧着他,实在令他难以欺近,他看了两瞬,冷冰冰的道:“将眼闭上。”
薄若幽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才将眼睛闭上,她后悔说他仁德,亦后悔说他至情至性,所为君心难测,现如今在她心底乃是侯心难测,而她身份地位在他之下,除了配合他之外还能如何?
心底腹诽着,很快,眼前一片漆黑的薄若幽察觉出一道属于霍危楼的气息在靠近,他的呼吸落在她面上,无端令她面上微热……
“本侯年少时便上了战场,战场之上刀剑无眼,军营之中更颇多细作,那时起本侯便有了枕刀而眠之习,后来到了朝中,虽说说一不二,可亦有那不长眼的。”
霍危楼缓声答了她适才之言,他每说一字,便有一道热息涌向她。
她闭着眸子,其余感官便格外清晰,她知道霍危楼靠的很近,而下一刻,清凉伴着粗粝落在了她颈子上,疼痛涌起本是寻常,可奇怪的却是一丝酥酥麻麻之感从她伤处弥漫开来,她落在身侧的手禁不住抓紧了身侧裙裾。
古怪,这感觉太古怪了,她虽不至于反感,却觉得有些难以忍受,她忍不住睁开眸子,果然,一眼看到霍危楼的眉眼在她咫尺之地,她心头极快的一跳,下意识将身子往后仰了仰,霍危楼手上一空,有些莫名且不满的看着她。
薄若幽也有些莫名,更未想明白自己为何躲,见霍危楼不满的看着她,便又往前靠了靠,霍危楼收回目光,只将伤药擦完,方才四平八稳的收了手。
“今日吓着你了。”
他将药膏递给她,想说什么却又住了口。
薄若幽接过药膏,见霍危楼神色有些复杂难明,便十分宽容的道:“侯爷不必自责,也是民女的过错,民女不知侯爷由此般习惯。”
霍危楼便看她,“往后可会怕本侯?”
薄若幽摇了摇头,心底却暗道,反正以后她也不会这般为他盖斗篷了……
霍危楼没看出她心底所想,加了一句,“以后不会如此了。”
您放心一定没有以后了!
薄若幽又腹诽一句,上了药不再那般痛,便抱着大人大量之心不想纠结此事,见天色实在晚了,便起身福了福,“时辰已晚,民女告退了,民女无碍,侯爷放心便是。”
说完这话,便等霍危楼应下,见她如此,霍危便点了点头不再出言留她,因他觉得此刻心潮起伏难定,再这般下去,不知还要生出何事。
门“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