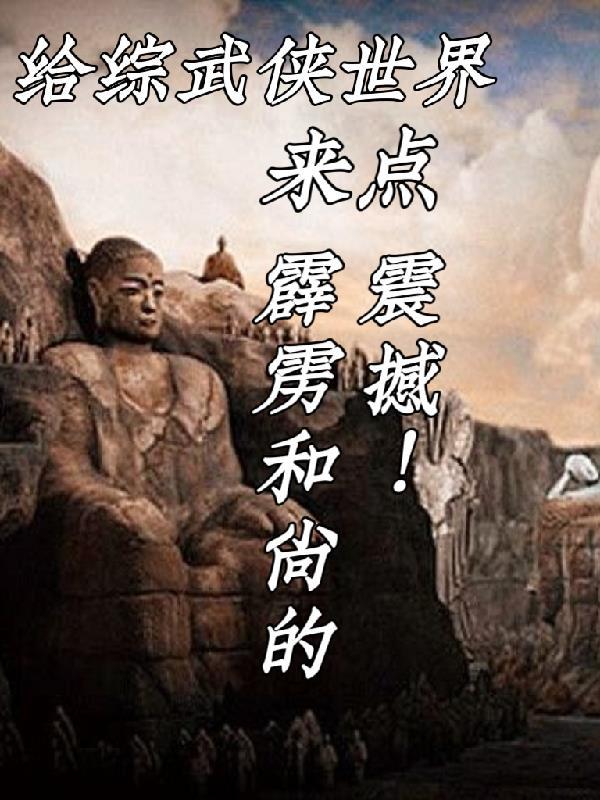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一杯酒的图片很真实 > 疯子(第1页)
疯子(第1页)
把门口的两个纸箱搬进来,拆开,一个室外机一个空气能热水器,都是上万的牌子。
安装完热水器,宋听雨还躺在床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身体在很小幅度地发抖。我掀开他的衣服给他处理胸口的伤,刺的很深,有玻璃碴掉进肉里,我拿镊子一点一点挑出来,再擦上碘酒,用绷带包扎好。
期间宋听雨一直盯着我的胳膊出神,袖子上的血已经干涸,透红的纱布完全粘在肉上分不开,我脱掉衣服去卫生间冲洗掉胳膊上的血,费力地把绷带从模糊的血肉上扒下来。
底下纵横交错的疤痕上是一圈圈烫伤,皮开肉绽,看起来狰狞可怖。笔画锋利的“宋”
字几乎被烟疤重新描摹了一遍,溃烂的地方流出恶心的脓水。
白瓷洗手台被源源不断的血染红,水龙头将血水冲进管道,面前碎了半块的镜子映出的上半身密密麻麻布满淤青,腹部的颜色最深。转过身,背后一片殷红,全是划破的口子,绷紧的肌肉上扎着数不清的玻璃碎块。
水声哗哗,宋听雨的身影闯入镜中,被裂缝分割成好几块。我们无声地在破碎的玻璃中对视,宋听雨脸上是四溅的血迹,眼皮、鼻梁、嘴边都有血珠流下,深蓝瞳孔还有些无神。
许久,他清冷的声音响起,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就像一个僵硬的机器人,“我咽下去了吗?”
我因为失血量突破正常值有点头晕,脸色也很苍白,我面不改色地道,“嗯,你咽下去了。”
在原地怔了一会儿,他缓慢地点点头,又抬起头说,“我想吐。”
宋听雨说着就要去抠嗓子眼,我没有阻止他,看他痛苦地干呕,当然,除了酸水他什么也吐不出来。
我走出卫生间拿镊子,折返回来时宋听雨蹲在地上捂着胃,我将镊子递给他,宋听雨没接,他不舒服地看着我,我说,“哥,一根手指而已。”
宋听雨被这句话刺激到了,他死死盯着我,眼中布满血丝,半天才咬出一句,“……疯子。”
我挑起一边眉,难得笑的温柔,“你说得对,是我。”
宋听雨胸膛起伏得厉害,他沉默着站起身,接过镊子。我转过去,他随时都可以将镊子扎进我的脖子,宋听雨自然也明白这是个不可或缺的机会。杀了我,他就彻底自由了。他可以将仓库当成避难所,直到有赌场的人来找他。
在他挑玻璃挑到一半的时候,我问,“是不想杀我,还是不敢杀我?”
宋听雨手下一顿,他哑着嗓子道,“宋秋迟,你怎么样才愿意放过我?”
抵在我后背的镊子在抖,宋听雨颤声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我为了活下去,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杨可?还是因为赌博?”
“哥。”
我抬眼看镜子里的宋听雨,沉声道,“谁接你出去的?”
宋听雨将镊子一摔,镊子磕到洗手台边飞了出去,他怒吼道,“有谁能接我出去?有谁?!谁会来救我?谁会来找我?是我自己出去的!我自己!!!”
他大口喘着气,双眼通红,眼泪一下滑了出来,“你满意了吗?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根本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我为什么出去了还要回来,你不是清楚的很吗?!”
我转过身看着他,平静地道,“我不清楚。哥,我确实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宋听雨吼道,“因为我他妈的爱你!!!我他妈爱你!你是我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
吼着吼着他哭起来,“我都这么爱你了……我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挖藏在后山的金条,借别人的手机买热水器,你想杀我,你还让我,让我吃你的手指……我都做了,你还是不相信我爱你……”
撒谎。
我冷冷看着他,宋听雨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宋听雨只要一进入市区,就会立马被监控捕捉到,何况还是在没有任何伪装的情况下。
仓库的门是从外面撬开的,铁链是被砍断的,凭床下那把刀做不到。
有人在帮他。
这个人没有立马带宋听雨走,而是又将他送回来,他们在利用这间仓库的极佳隐蔽性躲过警方的视野。
整合目前的信息,至少能确定那个人不能安全地带走宋听雨。
宋听雨在等,那个人也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离开,只要又一个“钟鼎”
成功建立,宋听雨就可以藏匿其中,再次做回“sapphire”
。
我怎么会让他如愿。
宋听雨默默捡起镊子,闷声道,“转过去。”
我没动,宋听雨蹙眉,他讨好地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下来,亲我的下巴和嘴角,吸了两下鼻涕,“小迟……你知道我爱你吧。”
我垂眼看他漂亮的睫毛,用指腹蹭他脸上的血,几抹殷红在羊脂玉般的皮肤上晕开,干净的东西要面目全非才好看。
“你问我怎么样才肯放过你,很简单。”
闻言宋听雨眼神中露出几分茫然,我说,“哥,你不是说爱我吗?那就给我我想要的爱。”
“……小迟想要的爱?”
我问他,“知道在疯子眼里,爱是什么吗?”
宋听雨问,“是什么?”
“毁坏、融合、取而代之。”
“而前两样你已经做到了。”
宋听雨怔了怔,我眼底隐隐显露出疯狂,同时冷静地道,“哥,你就是我,你是宋秋迟。你今年18岁,在落痕艺术中学学画画,背负着巨额赌债,你有一个养母,她对你很好,但你对她很疏离,因为你的亲生兄弟故意让你的养父在赌桌上输的倾家荡产,你恨他,你恨我,你囚禁了我。”
我将他的手放在我脖子上掐住,握着他的手用力,“你3岁亲眼目睹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强奸,那个强奸她的男人成了你的继父,他吸毒、家暴,无数次殴打强暴你的母亲,还逼她也一起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