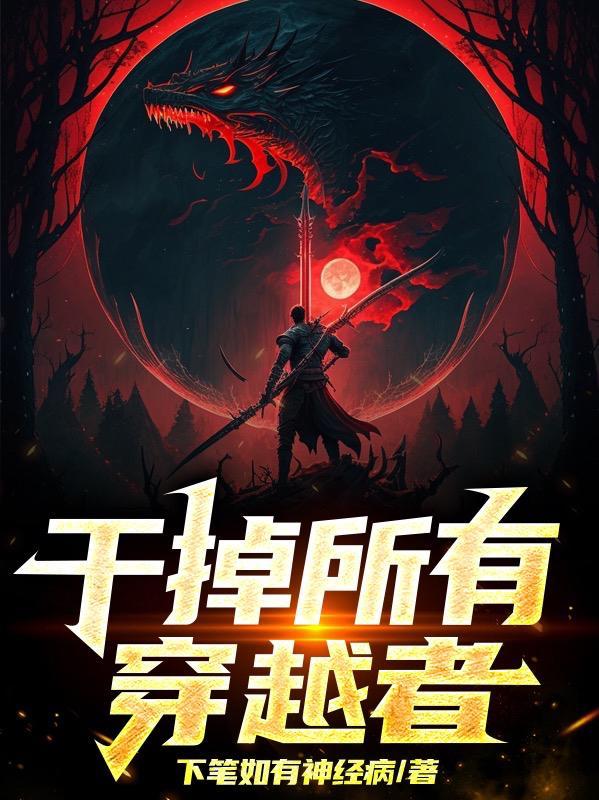69书吧>春来雪未泮 > 重生(第1页)
重生(第1页)
宣德二十一年,冬,三日大雪,玉琢银装,大雪盈尺。
大雪下的恒德王府内,奉神外守着俩个侍女。
在檐下拉紧了身上的披肩哆嗦道:“听说了吗?恒德王造反处决下来了,三日后处死。”
另一个侍女不敢相信:“啊?不能吧?前几年大殿下逼宫谋反都没被处死,只是囚禁,那三殿下乃是中宫皇后所生,大殿下连生母都没有,母族还无人都没被处死,怎么三殿下会?”
“这就不知道了,我听说讣告都下到各各衙门了。”
“你说这皇家,总共三个皇子,俩个造反,这是什么事啊?不过这以后的天下恐怕就是二殿下和容家的了。”
另一个侍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平底鞋,上面脚尖处还因为雪被弄湿了:“管他是谁家的反正也落不到咱们头上,咱们这些小人物就只管埋头干活吧。”
“那。。。。。。。”
其中一个侍女瞟一眼身后的奉神小声说道:“那王妃的处决是不是也快下来了?”
另一个侍女也望像奉神,妄想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的人———恒的王妃顾勇冰。
自从三殿下被抓,下入牢狱,这恒德王府就被控制住,所有人都被下了天牢盘问,唯独这王妃没有,想必是因为她的父亲是朝中一品大夫,祖父更是为救先皇而死,圣上不便处决吧。
圣上念在这份上没有太大的限制自由只要不出府就行,还让她们这几个贴身的侍女伺候,可见顾家在朝中的地位。
只不过自从被封府,恒德王妃除了吃饭睡觉就只呆在这里,一跪就是一天。
侍女无奈叹了口气:“不知道啊,不过这世间女人也是可怜,嫁人随夫,只管内事,外事不得管理,确偏偏丈夫犯事自己毫无关系也要受罚,到头来只落得一句约束不严,可当今又有几个女人敢约束自己的男人,又有几个男人会听女人的劝诫。”
有时候只有女人懂女人的苦,就算一个贵为皇亲一个贱如奴婢,可同是身为女人,历经的苦楚也几乎无异,无非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一辈子都拴在男人身上了。
恒德王府内外重兵看守,外面的士兵穿盔戴甲,黑泱泱的一片,就连街道都封死,不让任何人进出。
可却有个马车突兀的行来,在这硕大的街道上流下唯一的印记。
马车停在府前,看守见状,手扶着腰间的佩刀呵斥道:“来者何人!”
道路封锁,能被道路关口放进来的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皇命,所以侍卫态度不敢太过强势,要不早就乱箭射死了。
待马车稳定下来,自上面下来一位女子,清冷的面对这些官兵无任何胆怯,自然的在袖口掏出一块令牌,那些官兵见到领来立马跪下来。
那女子平淡的说道:“让开。”
“是。”
府门被打开,这是被监管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被打开,女子抬头看了眼悬挂在上的【恒德王府】,最终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迈了进去。
恒德王府没了往日的热闹,连个人影都不见,女子一直沿着长廊往里走。
走了好久,直到在奉神外才终于看到有两个侍女在门口。
奉神中供奉着一尊高大的金佛,佛岸上依次排列着十二尊佛位,每尊佛面前都摆着一盏蜡烛。
恒德王妃顾勇冰此刻正双手合十,跪在佛前虔诚的祈祷着,烛光一晃一晃的打在女子脸上,散出一种诡异的美。
“吱嘎。”
……
“吱嘎。”
门被推开,一股寒风涌进,进门的女子抬手拂去肩上的雪,便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奉圣上意前来审问你。”
顾勇冰没有理她,依旧闭着眼睛,盘着手里的佛珠。
女子走进,烛光也照在了她的脸上,二人居然有几分相似,抬眼看着被蒙上眼睛的佛像说道:“以为蒙上了佛祖的眼睛,就看不见你犯下的罪孽?又或者是你根本不敢直视佛的眼睛。”
盘着佛珠的手顿了顿,停了片刻之后又像无事般重开始。
看着跪在地上依旧不痛不痒的人,女子怒火中燃,把拿在手里的画卷扔在她面前。
“恒德王把所有的罪责推到你身上,推在顾家身上,说是同顾家共同勾结外邦,容家借机难,这便是在顾家搜到的证据,画中藏于东吴国勾结的暗信,是你亲自送到顾家的,在母亲生辰那日,顾家一直保留到现在。”
顾勇冰这才睁开眼睛,打开画卷,画卷中间被撕开,里面的信应该被上交了,看了眼上面的画,愣了一下,脑海中闪过一丝,随即却自嘲的笑了起来。
“你要问什么?”
顾勇冰扔下画卷无力的问道。
“你送画的时候究竟知不知道画中夹杂着密信?”
“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结果会改变吗?”
顾勇冰回道。
“这次谋反你是否参与,参与多少?”
顾勇冰毫不掩饰:“参与。”
“多少?”
顾勇冰沉默不语。
“是否被迫?”
女子继续追问道。
回答她的仍旧是一阵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