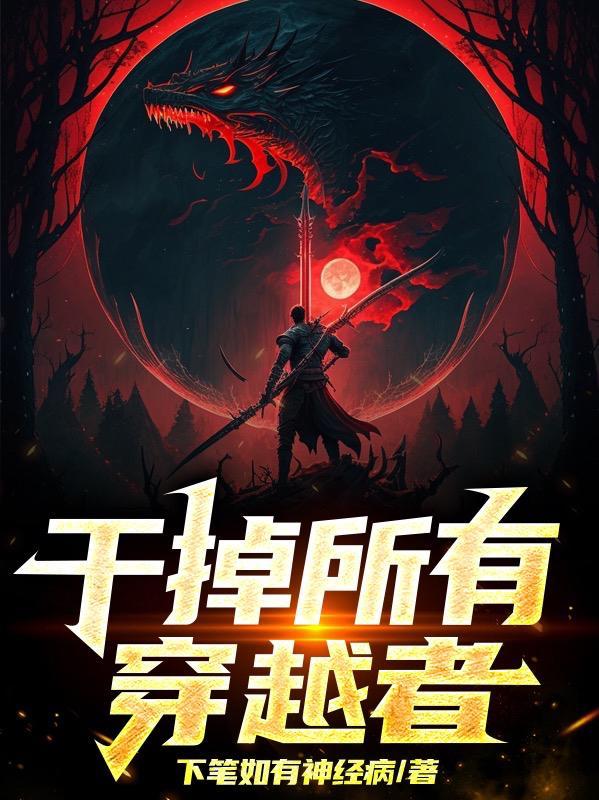69书吧>女公子图片头像动漫 > 第22页(第1页)
第22页(第1页)
然而就算这句马屁也并不使人满意。景龙的眼睛又眯起来,明明白白的嘲讽之意。
“我已当着百姓的面杀了妇人。哪个傻子会觉得我有什么‘厚德’?”
他声音低沉震耳,虽是雅音,却染了北地的粗犷音调,
赤华呼吸紊乱了一刻,不慌不忙答道:“那是太子一时冲动,谓之过;而若再杀此孩童,便是深思熟虑之举,谓之罪。妾将为徐国妇,若眼见夫君有罪而不谏,是为不忠不贞,那也不配再往前行了。”
胆大的百姓们凑上来三五个,听到赤华此言,此起彼伏地抽冷气。
有生之年,没听说有人敢跟太子这么不敬的,还直言什么“罪”
!
不过……人家是荆国贵族,未来的太子妇,就算口无遮拦,大约也会获得一些豁免的特权吧?
看她的面颊娇嫩如花,身段美妙如玉,口中如吐芳兰。再不近人情的鞭子,也不忍心毁掉这样一件珍宝吧?
荆旷几次欲言又止,恨不得亲身上阵,替她说几句软话。但他也看出来,景龙虽然偏执,却不是好糊弄的傻瓜蛋。自己冒然打圆场,万一赤华这丫头不领情,跟他唱个反调,连带着他公子旷今日被全徐都百姓看笑话。
他只好看看徐朔,带了些不情不愿的求助的意思:要不你劝劝你兄长?
徐朔却无动于衷,拉着个长脸,嘴角依旧向下撇着,甚至低头玩起了袖口的一根抽丝,摆明了眼不见心为净。
难堪的寂静持续了多时。景龙久久不语,久久打量着赤华。
忽然,他冷笑,随后开始大笑。几个百姓吓得连连后退。
“呵,荆侯长女,果然不是一般人。只听说她身体孱弱,想必性子也是弱的;今日一见,却是两者都错了,哈哈!倒是个惊喜。”
赤华不愿他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再次行礼:“那么那孩子,太子是饶了?”
景龙冷笑:“你拿什么,换他的命?”
“妾身的一切,今后全供太子差遣。”
景龙盯着她细长的眼睫,一字一字道:“今日你是荆国公子,我可以给你面子。他日再见,我不希望再有人拂逆我的意志。”
他不等赤华答话,翻身上马,打个手势。后头的随从和犬奴随即跟上。
他虽然以草菅人命为乐,但那也仅限于无足轻重的贱民之命。他是堂堂一国太子,又不是疯子。
不过,内心的暴躁总归无法宣泄。他回头看自己的随从。一个倒霉鬼动作慢了些,被他狠命抽了一鞭子。
那人痛得彻骨,却也不敢出声,哭丧着脸,狠命夹马肚子,也跟上了。
一阵高高低低的唿哨,猎队转眼间疾驰不见。
街道忽而寂静,只有被灰尘呛到的、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赤华扶着小多的手,快回到车上。余光似乎看到几个百姓伏了地,朝自己磕头。
*
当晚,公子旷被请到徐宫里赴宴;“公子瑶”
一行人被安顿在城郊住下。
赤华举目抬头。她面前是一座华丽高台,青石为阶,白玉为栏,宫灯摇曳,檐牙高啄。顶层似有一露台,托着初升的弯月。
已有一队徐国侍者等在阶前,男仆女奴老媪一应俱全,见了赤华,规规矩矩行礼。
他们大约已听说了白天里,荆国女公子曾与太子景龙对峙劝谏之事。此时见了真人,又是如此年少而明丽,更是对她佩服有加。
管事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无姓,名良,赤华便称之为良姑。
良姑已把她当本国夫人看待了,嘘寒问暖,极是热络。夜色微凉,又张罗给她取大氅——好像她没从荆国带厚衣服似的。
赤华问此为何处。
良姑答:“国君为太子迎娶妇,特意在东郊修建象台,作为夫人的婚之所……”
赤华脸一红。有人轻声提醒良姑:“叫公子!这还没成婚呐。”
良姑笑呵呵改口:“……哦,是是。这台有些高,还要累公子举步上去。”
当前王公贵族们流行筑台,高耸的夯土为台基,上有建筑房屋,以供居住、宴饮、取乐。筑台不易,往往需要征召平民,花费大量钱物。若是有幸国力昌盛,筑台比别人高大,还得找个名头,请些公卿贵族前来观赏,收货赞美和艳羡。
登台而远眺,是最能让人感到高低贵贱之分的时刻——平川无垠,良田起伏,庶民忙碌奔波如蚁,城墙哨兵来往巡回,而台上之人把酒临风,不饥不寒,谈笑间决定万民的生死,瓜分天下的膏腴。
赤华仰望象台。傍晚风急,吹得她裙摆飞扬,绝尘而独立。
夕阳在她侧后方,映红了她的耳廓,也将那高台照得格外辉煌,像一个披了金甲的巨人。
荆国没有这样的高台。她感到有点压抑,喘息艰难。
从踏入徐国土地的一刻起,她便被一种别扭的感觉包围着。徐国的礼数不可谓不周全,派司徒公子朔接亲,所选的都是万里挑一的宫廷护卫,一路饮食起居都无可指摘,比她在荆国时还奢华。
但公子朔始终不咸不淡,对荆旷没有对“亲家”
的热络,对赤华也没有对长嫂的恭敬。他仿佛是不情不愿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把赤华安顿好,急着甩手走人。
赤华仔细想了想,一路上她没得罪这人。荆旷的确跟他相处不谐,但也是他目中无人在先,并非己方失了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