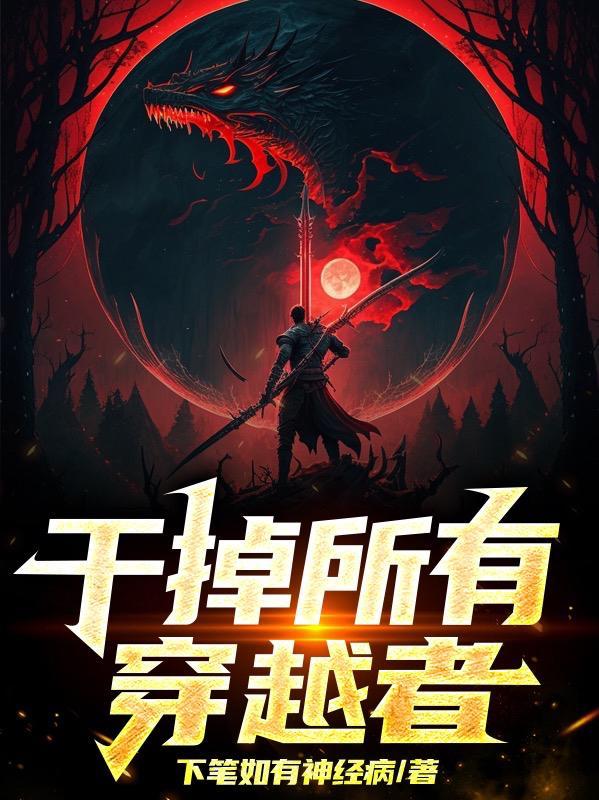69书吧>女公子图片头像动漫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好在弓箭手已不敢冒然放箭。夏偃矮身滚地,用尽他平生的目力和敏捷,躲过一次次劈砍,用手中的剑给自己开路。
有人的脚被斩出鲜血,丢下手中武器,嚎叫着跌倒在地。
而夏偃也并非铜头铁臂。飞蛾扑火的那一瞬间,手臂、肩背、腿脚,便开了五六条细细的血线。他快得像一阵风,没给旁人留下攻击他要害的机会。
但流失的血也带走了他的力气。他轻轻咬自己舌头,用丝丝缕缕的疼痛,将身体里那副拉到极致的弓弦,硬生生又撑开三两分。
当此千钧一的时刻,每个人都是赌桌上的豪客。每一个招数和战术,都左右着赌局的平衡。
不同的是,有些人的赌注只是他的一双腿脚;受了伤,便只好退出。
而夏偃,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命。
还有除了性命以外,他所拥有的一切。
荆侯惊恐地看到,一团旋风以惊人的度劈开他身边的重重护卫,身后留下一道斑驳血印。
他倏然跃起身,手中的剑已断,却舞得狰狞,像一条泥泞里挣扎的怪鱼,龇牙咧嘴地冲向一滩污浊的水。
荆侯拔出身边佩剑。镶金嵌玉的手柄,沾了汗,却无端的滑。试了几次,那剑像是锈在了鞘里,居然纹丝不动!
再一抬头,冲鼻一股鲜的血味。一张血汗流淌、狼狈不堪的年轻面孔,两只眸子凶狠而透亮。
*
夏偃剑刃碰到荆侯的华美深衣的那一刻,禁卫们噤若寒蝉。
贵人多怕死,用层层武装在自己身边筑了高墙,缩在里面像只龟。
然而龟壳虽坚,一旦突破了最后那道防线,就会现,里面那坨瑟瑟抖的软肉,原来和常人一样不堪一击。
在这一点上,荆侯和董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同的是,董肥靠金钱拼杀江湖,肥硕的外表下,尚且包裹着一颗带着野性的心,让他相信,这世上有比自身安危还要值钱的东西。
但荆侯不同。他已站在人生制高点,稍微下滑一步,便是输不起的万丈深渊。
荆侯不敢低头,两只眼珠子拼命往下翻,看到一只带血的手,勒着自己的脖子。
下一刻,才感到呼吸不畅。他艰难地用力张开胸腔,脸色白如霜雪,恰如重病时的公子瑶。
“叫你的人把她放了。”
耳边响起急促的喘息。
并没有杀人伤人的意思。荆侯这才似乎突然回过神来,摆正一国之君的姿态,怒不可遏地叫道:“那你们先放了寡人的女儿!”
夏偃一边卸掉荆侯腰间那柄珠光宝气的佩剑,一边冷冷道:“若非我们救她出来,她在楼上,已经烧死了!”
荆侯哼了一声,不言语。这个女儿他已经几年没见,印象里那个绕膝承欢的活泼女孩,音容笑貌早就模糊不堪。刺客来得那么快那么急,他哪有功夫想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