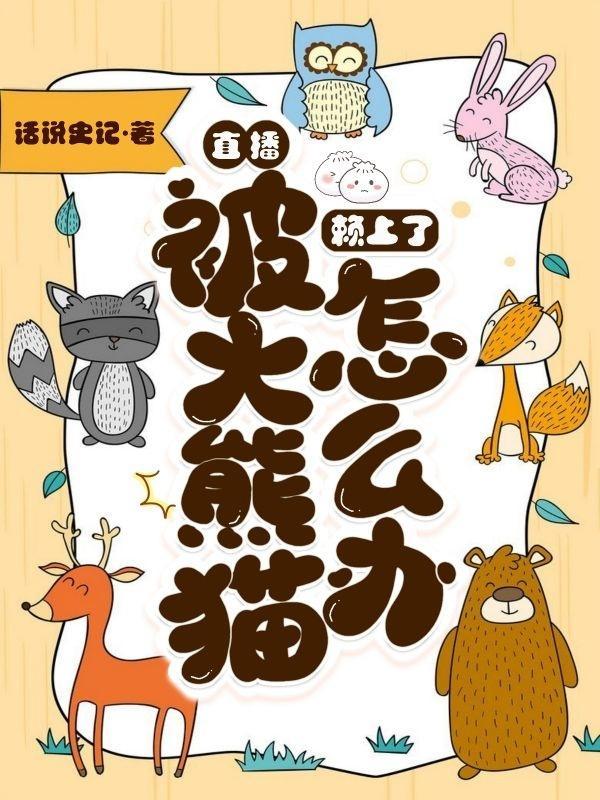69书吧>比邻整数 > 第60节(第2页)
第60节(第2页)
赵启世安坐在椅子上,神色不改,不过语调明显提高。
“是刀伤,已让郎中缝合、包扎。”
本想遮掩,还是被发现,赵启谟老老实实回答。如果他有十分怕老爹,那就有六分怕老哥。
“如何受伤?”
赵启世进入仕途,手中办案无数,他不只眼尖,还很会揣度他人心思。
赵启谟一阵沉默,这事实在没法说。
“若是他人伤你,我自不饶他;若是你与人互搏,我也不饶你。”
赵启世这话,听得女婢收拾衣物的手一抖,他声音冷厉,寒气逼人,往时佥判官人虽不爱笑,但言语温和。
“与人互搏。”
赵启谟一阵沉默后,终于还是开口承认。他这人错便是错了,在父兄面前,他也不擅长遮掩。
“此事,我必然如实告知家父。”
和人打架斗殴,犯老赵家大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赵启谟刚蒙学那会,就该懂得这个道理。
“去唤秦大夫,让他即刻过来。”
赵启世看向门外,朝站在门外的仆人说道。门外两位仆人端水、拿巾,见官人言语严厉,不敢进来,内知也候在门外等待差遣。“老奴,这就前去”
,内知领命离去。
“太母让我务必将你看顾好,可如何跟她交代。”
赵启世轻轻叹息,现下还没拆开伤口,不知道伤成怎样,即将回京了,却要带着伤回去,他做为兄长被念叨便算了,太母一把年纪,还要为这宝贝孙子心疼、难过呢。
那便不要让她知道。
赵启谟心里嘀咕,不敢说出口。
见赵启谟低头不语,想他会好好反省,又受着伤,赵启世也不好将他怎么着。
骂也没用,打更不该,他已是十七岁,该明白的道理自会明白。当然,也不能就这么轻饶他。
“回京前,你就在这屋内养伤,哪也不许去。”
赵启世留下这么句话,起身离去。
待秦大夫过来,赵启谟已沐浴更衣,默然坐在榻上。屋内不只他一人,哥哥嫂嫂也在。
“舍人,请将手臂抬起。”
秦大夫是城东有名的大夫,对赵启谟也是客客气气。
赵启谟抬起手臂,女婢过去,将他袖子卷起,一层层的卷,赵启谟穿的衣物多。终于袒露出手臂,呈现包裹的细麻布。
秦大夫剪开细麻布,他的手法轻巧,比南澳那位郎中高明不知多少。
细麻布拆走,露出缝合后的伤口,看着吓人,嫂子杜氏轻啊一声别过头去,赵启世冷静看着,问大夫:“这样的伤口,几日能拆线?”
秦大夫端详针脚,缓缓说:“缝合手法略有些粗糙,也不知用的什么药水,我这边重新抹药包扎下,四、五日后,便可拆线。”
“日后若是留下疤痕,可有法子医治”
赵启世担心着,好好的一只手臂,留下疤痕可怎么好。
“也有医治的法子,官人不要着急,急不得一时。””
秦大夫轻笑着,心想世家子是极在乎身上留下点疤痕,这伤在手臂,狰狞可怕,夏日都不好穿短衫。
秦大夫为赵启谟重新涂药,包扎伤口,并写上几帖药,细细交代如何煎药,几时服用最佳。赵启世拿走药方,出去吩咐仆人抓药。
此时房中,只剩赵启谟和他的贴身小童阿鲤,以及收拾医箱正要离去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