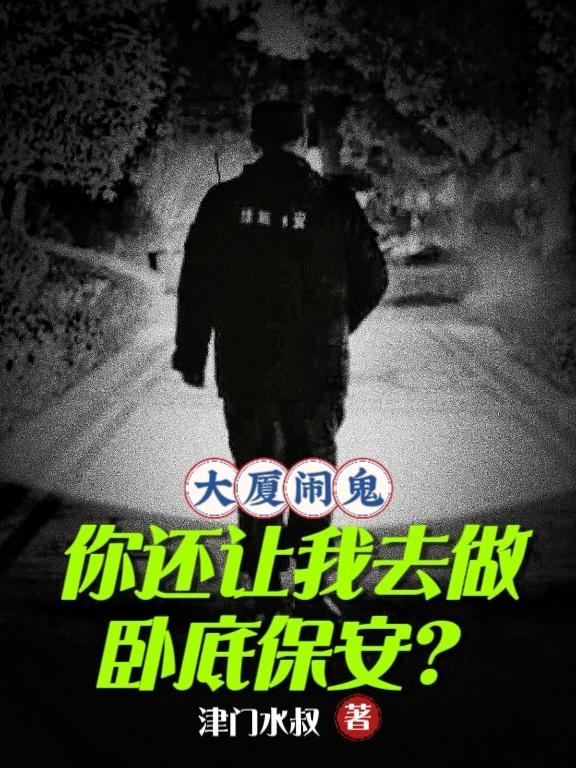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重生之再嫁皇叔韩攸宁 > 韩钧X陈蔓番1(第3页)
韩钧X陈蔓番1(第3页)
赵承渊微笑道,“小婿来给岳父大人出出主意,如何抱得美人归。”
韩钧冷哼,“才不信你的鬼话!这一年多来,你前后到底瞒了我多少事,骗了我多少回!”
他语气一顿,睨着赵承渊,“什么主意?”
赵承渊:“苦肉计。”
韩钧嗤笑一声,“苦肉计哄女人,非君子所为。”
他拎起墙根下的长剑抱在怀里,往院子附近的树林子走,“你过来。”
禅房有三间,布置得朴素。
陈蔓拉着女儿进了内室,从榻上拿起来一件粉嫩的春衫,还有一条天青色的襦裙,衣裙上散落着轻盈的桃花。
她笑着道,“你换上,看看合不合适。”
韩攸宁眼圈泛红,她虽盼着穿母亲亲手缝的衣裳,可如今母亲日夜受着病痛折磨,哪里来的力气做衣裳和绣花……
她接过衣裙,在秋叶的服侍下默默换上。
秋叶惊叹道,“娘娘,您穿着这衣裙可真好看,像仙女似的。夫人,您的手可真是巧!”
秋叶一向讷于言,不似铃儿那般伶俐。来母亲这里半月,她却学会夸人了。就像前世,在韩攸宁身边只剩下秋叶一人时,她变得聒噪得很,比铃儿还要活泼。
韩攸宁张开双臂美美地转了两圈,“你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陈蔓帮女儿整理衣襟,笑着问,“可有哪里觉得紧了?我再给你改。”
韩攸宁:“不用改,正好合适,穿一个整个春日没问题。”
陈蔓笑看着她那尚看不出隆起的肚子,“哪能穿得了一个春日。再过一个月,肚子就显怀了,衣裳都得重做。”
她拉着女儿到榻上坐下,脸上洋溢着慈爱的笑意,“我怀你的时候,常常是衣裳做好了还没上身就小了。你父亲还说……”
陈蔓停了下来,脸上的笑意收敛,低头叠着韩攸宁刚刚换下来的衣裳。
韩攸宁轻声道,“母亲,父亲这些年过得苦,您便当可怜可怜他。”
实际上,父亲苦了整整两世,甚至上一世更是凄苦。带着记忆活着的人,总是要更苦一些。
陈蔓沉默着叠衣裳,叠好之后整整齐齐放到一旁,方道,“你父亲年纪尚轻,再找个好人家的女儿也不难,我又何必耽误他。”
“母亲这话就说错了,父亲若是想续娶,何必等到现在。他不就是忘不了你吗。”
韩攸宁拉住母亲的手,“那些所谓的贞洁,父亲压根都看不在眼里。母亲,您就莫要画地为牢,自己将自己囚困了。”
陈蔓抬手抚摸女儿的脸颊,笑道,“我在那副《秋山图》上看到你写的一句‘攸宁的师父是个大懒虫’,心里就想,我女儿真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如今看着,怎么还老气横秋起来了?”
韩攸宁早就体会到了,母亲实则是个颇有主见的人,轻易不会改变心意。
旁人劝是劝不通的,只能如赵承渊所说,靠父亲自己一点一点去软化。
母亲受了太多苦,只有父亲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她才能慢慢放开心扉,接纳现在的自己,也接纳父亲。
韩攸宁不再劝,说起去襄平府寻玄智大师的事,三日之后便可出行。
陈蔓听了,没有反对。陈府受她连累倾覆,她是该回去,好好祭奠父母兄长。
她小时候便在沧源山长大,在那里终老也不错。
佛法,总能荡涤去些许她身心的污浊。
韩攸宁窝在母亲怀里又腻歪了许久,眼看着日薄西山,方起身与母亲辞别。
陈蔓面上不显,心里却是万分不舍女儿,她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三日后离别,不知还有没有再见女儿的机会。
如此想着,虽不想见韩钧,她还是送女儿出了院门。这是半月来她第一次出院门。
院门口不见韩钧和赵承渊的身影,倒是不远处传来打斗声。
母女二人循着声音走过去,却见树林那边翁婿二人打得难舍难分,韩钧招招狠辣,赵承渊苦苦避让。
韩钧余光看到陈蔓的身影,胳膊便往赵承渊的剑上一凑。
他闷哼一声,手臂上便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韩钧剑眉紧皱,捂着伤口面色痛苦。
赵承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