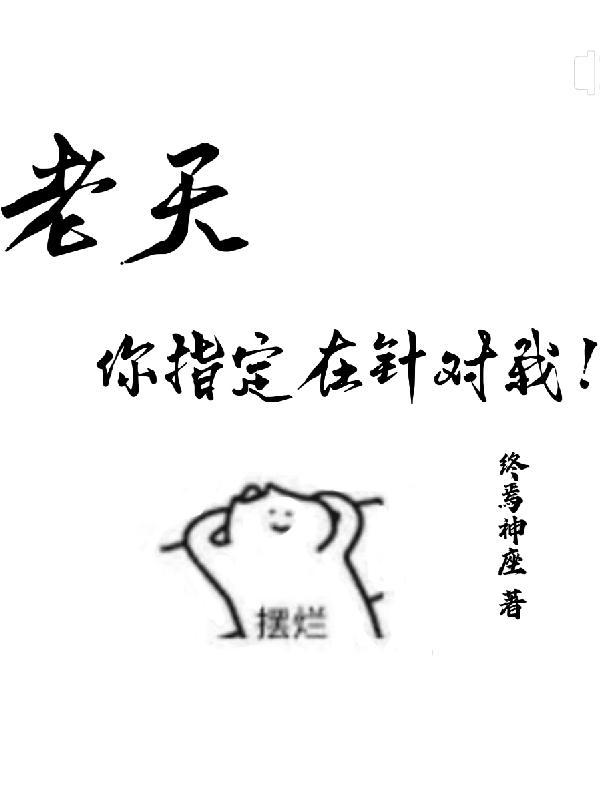69书吧>朋友妻来世可妻砚心女官免费阅读 > 第22页(第2页)
第22页(第2页)
太子压腕斟茶,不在意道:“每日都来,所言无异。”
男人之间的关心总是该点到即止,太子自若,沈则也不好多言。
茶香弥漫,太子轻嗅一口,眉头舒展,看向沈则:“长宁既已及笄,婚事就近在眼前了,你一直躲也不是办法。”
“我没躲。”
沈则捏着茶盅,说的认真,“只是眼下荆州不安定,我也无心想这些事。”
他说的算是一半的实话。至于剩下那一半,他究竟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想到了哪一步,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太子吞口热茶,呼气道:“明年底,怎么说荆州也该料理清楚了。”
说完,他突然抬头,问沈则:“你今年二十”
“是。”
“了不得啊。等你明年平了司空乾,保了荆州一线的安宁,就是大梁最年少的大将军。”
这一番话,字字落地,说得板上钉钉,仿佛那是没有第二种可能的事实。
“我要是平不了司空乾呢?”
沈则将喝空的茶杯往前一推,像是随口问了一句。
“我在这儿吊死,”
太子抬手指顶上房梁,嘴角却噙着笑。
“那我呢?”
“你是不必自己动手了,自有司空乾送你上路。”
“你还是不信我能带他回来。”
“我不信,劝你也别信。”
这样的对话不是头一回了,每次说到最后都是相同的沉默。
-
越近正午,天色愈暗沉,黑云压在头顶,把白昼遮成黄昏。滚滚惊雷之后,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砸下来。
陈茗儿弯腰护着怀中的包袱,快跑两步,躲进了街边的歇脚亭。此刻,她也顾不上自己被打湿的衣衫,忙去翻看怀中的布料是不是淋了雨,见布料完好,这才舒了口气。
刚才跑的那几步,只顾着照看怀里的东西,踩了两脚水坑,鞋袜湿透,襦裙下摆裹着泥点子粘在小腿上。风逐着雨灌入亭中,陈茗儿猛地打了个冷战。
四周是遮天的雨帘,连商户都纷纷掩了门,目之所及,竟再找不到另一只落汤鸡了。陈茗儿将身子蜷了蜷,其实风并没有变大,但她着实觉得更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