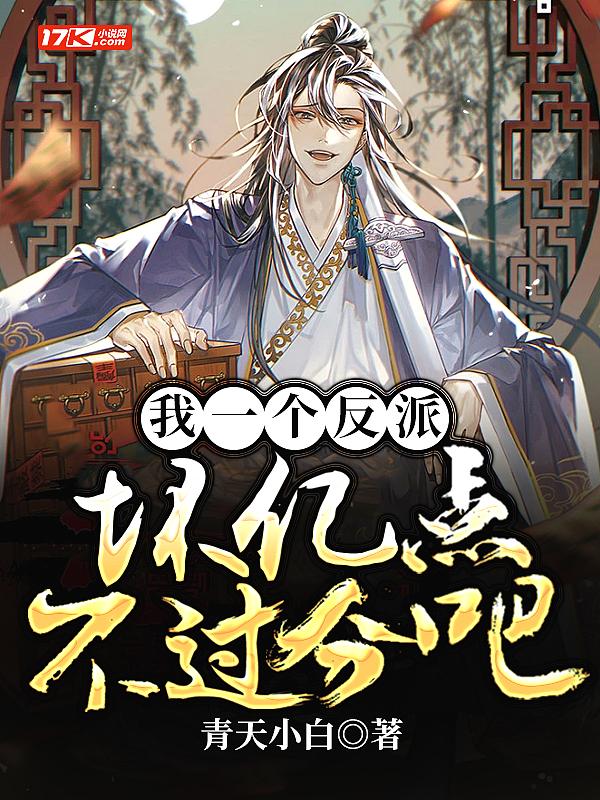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与卿安意思 > 第八十章 结伴商客(第1页)
第八十章 结伴商客(第1页)
黑夜过去,清晨悄悄来临,天边刚刚露出鱼肚色,清容早已醒过来,洗漱整装,准备出了。
她出了驿馆,翻身上了自己那匹枣红色的大马。此时日头已经升起,可晨间的风还带着凉意,吹得人鼻头红。她眯着眼,望向远处的草原,这里是距都城千里的云州,与雍城的景色大不相同,大片大片的草原映入眼帘,广阔无垠,出了这座城,便要路过那祁山脚下了…那又是另一番景致。
望着这片陌生又开阔的景色,她既觉欣喜,可又不免多了几分不安和担忧,直到薛常和阿珍打马转到了她的面前,看着这几张熟悉的面孔,她的心才踏实了几分。
一行人打马驶出还没有多久,一个胡人男子便打马追了过来,高声喊道:“娘子留步!”
清容回眸,她不曾见过此人,来者身着胡服,卷褐眸,轮廓深秀,俊美异常,看着年纪不大,整个人却透着一股精明的劲。
薛常先认出了昨日那个领队,他上前与他打了招呼。
清容带着面纱,只露了一双眼睛在外,安七郎霎时一顿,随即回神笑了笑,他上前笑着打招呼道:“某姓安,是昨日商队的领队,昨日多谢娘子相助,昨日匆忙,未曾给娘子备下谢礼,今日一早某便赶来,还望娘子笑纳。”
说着,就让人递上一个沉甸甸的黑盒子,清容弯了弯眼眸,微笑道:“举手之劳,安郎君不必放在心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实在不必如此破费。”
安七郎笑说道:“我看娘子谈吐举止不俗,像是官家娘子,自然是见多识广,可是看不上这等俗物?”
清容摇头,道:“安郎君实在太过客气,都是在外奔波之人,不过见人有难,伸手相助,想结个善缘而已,安郎君不必放在心上。”
安七郎见此只好让人将东西收了回去,清容又道:“若是有缘,说不定在西州我们还会遇见。”
他眼睛一亮,接过清容的话道:“听闻娘子此行也是去西州的,正巧是与我们一路,这还有一个月的路要走,不如结伴而行,也好相互照应。”
昨日他自听说了清容是住在驿站的,便心里有了盘算,这驿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里头的都是有身份的官家人,身份自是不一般。他跟着家里的长辈来往雍城和西域做生意多年,耳濡目染,也会识人,今日又见清容的举止气度都不似普通人,便动了结交的心思,对于他们这些商人来说,若能结识贵人,自是多些财的门路,有谁不愿意呢?
薛常看着他,一时觉得不太对劲,心中不免腹诽道,到底是谁照应谁?可别给他们添乱才是!
谁知清容竟也答应了,那安七郎又借着顺路为由,一直跟着清容身边,就着西州的风土人情,与清容一直说个不停。清容知道这胡商打的什么算盘,但想到自己也是初到陌生地方,人生地不熟,也想多做些准备,因而也乐意与他同行。
“娘子是初去西州,那定是对西州不甚了解吧,我家世代在西州为商,若是娘子有什么想知道的,问我便是。”
清容温颜一笑,“那我便却之不恭了,我初来此地,又见安郎君汉话说得颇为流利,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知道依安郎君看,这西州,龟兹哪儿更好呢?”
安七郎想了想,说道:“哪儿最好?这却是不好说,这西域地广,各有各的特色。”
“哪…是何处汉人最多呢?”
“龟兹胡风最为浓郁,汉人也少些,西州商旅,三教九流之辈最多,鱼龙混杂的,这庭州气候不好,可却是汉人最多的地方,不知娘子更喜欢何处,只是这几处地方离得也近,来回最多也不过几日的脚程,娘子若是得闲,都可去瞧瞧。”
清容笑着点点头,“原来如此,多谢安郎君。”
两人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清容竟是十分感兴趣,问完这又问那,将这风土人情也问了个七七八八。
薛常在后头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这安七郎人能说会道得很,又生得俊美,还时不时地和娘子故意套近乎,而娘子又是这一副和善,笑语晏晏的模样…他蓦地想起昨日去帮忙时,听到车队里的人打趣时说的话,一时心中警铃大作!
从云城往西行了四百余里,便到了西北地带,已经行了快半月的路程。
“娘子,你快看!”
阿珍坐在马车前头,连忙唤骑着马的清容,声音里是藏不住的惊喜。
清容顺着阿珍指向的侧后方,蓦然一愣,一时竟难以形容眼前之景:山脉延绵数百里,层层叠叠,在如此干净的蓝天之下,映着骄阳的光,壮丽磊落的不像话!她想起蔺衢子曾在提起过出游西域时也曾路过此地,她一时失神,望着远处,看了好半晌,才道:“原来竟是如此景色!”
安七郎此时也打马过来,见清容一副失神的模样,笑道:“这景色如何,娘子在雍城多年,不知可有见过这般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