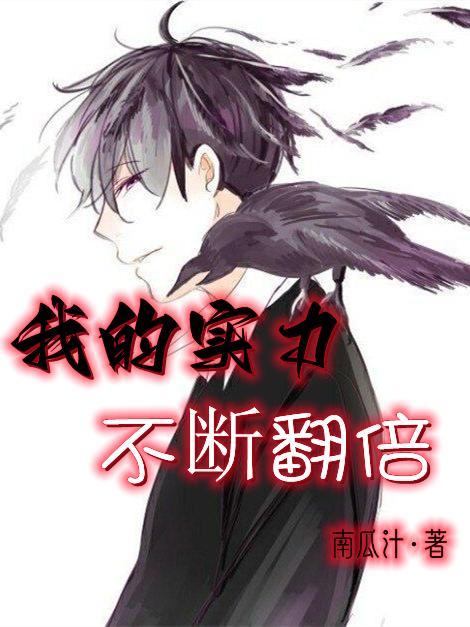69书吧>反派兼职男主室友后曲破寒川 > 第20章(第2页)
第20章(第2页)
不久后,唐烛将她送走。
他站在大敞着的黑色铁门里,目送马车消失在道路拐角。
背后余温未尽,手臂伤口上临时涂抹的麻药慢慢失去疗效,卷土重来的痛感越加清晰。
他抽了口冷气,原地踱了几步,却没能走远。
毋庸置疑的是,他仍旧对阿亚尔那句“您很了解他?”
耿耿于怀。
唐烛原以为自己早已获得先机,他比这世界中的任何人都要率先了解付涼。
因此他相信自己能借助于此,预判对方的心态与处事方法。
但当他与一双如此冷静的眼对视时,完全没预料到他即将看到的是什么。
像书中那位名声远扬的天才侦探初次登场时,对亨特警长说的。
“时间在身体上划开的伤口,永远不会愈合。”
唐烛摸了摸自虎口蔓延而上的旧疤。
记忆中,他的身边从没有过时刻陪伴的朋友或爱人。换句话说,从来不会有谁了解他那段成名前不堪回的历史。
付涼的质问,带给他不切实际的错觉。
像是很多年前,他们就认识。
……
当他陷入比灰烬更难复生的回忆时,圆形焚尸台旁已经多出了一个人。
促使他回过神的,是眼前木炭上多出的一张信纸。
唐烛顺着燃烧的纸张向上,找到了一只修长的左手,裹着昂贵西服的手臂,与一张情绪依旧寡淡的侧脸。
因为不久前的对话,使他难以开口寒暄,只得站在原地看着那封熟悉的信消失在风雨里。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付涼完成了不像样的“祭奠”
,拍了拍手打破沉默。
唐烛有些吃惊,更多的是疑惑:“你、你说什么?”
他甚至转头四处张望了一番,确定此刻附近只有他们两人。
对方另只手里还有一把未打开的伞,语气略显不耐烦:“你已经送走他们两个了,可以回去了吗……”
不等他误解,付涼又道:“维纳让我来找你。”
“或许……是因为我刚刚在船上找你,其实、其实也没什么事,我只是——”
“并不是因为这个。”
青年无情打断,一双漆黑的眼转而看向他。
“那……”
唐烛被盯着,紧张到几乎感觉不出身上隐隐作的痛楚。
以付侦探敏锐的观察力,当然能察觉出他的警惕,可惜他还是没选择把视线收回去,继续说:“他想邀请你去度假,让我转达。”
唐烛以为自己耳朵出现了问题:“……啊??维纳大人……邀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