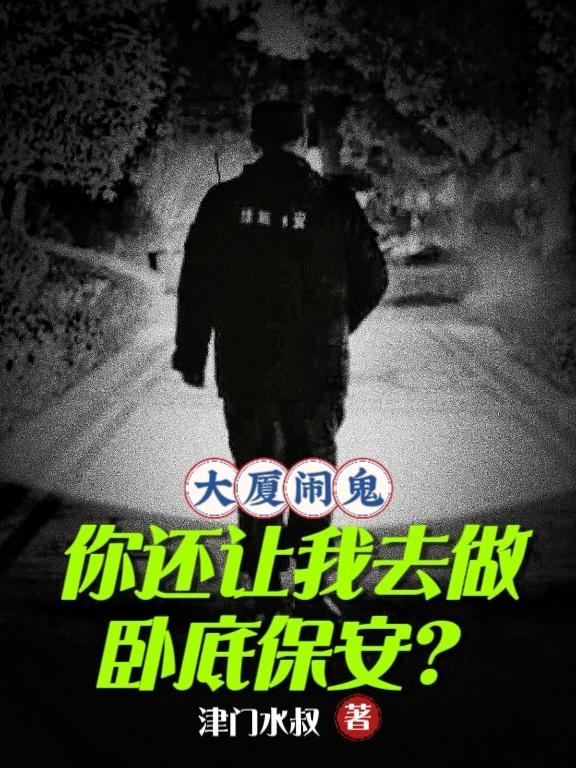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凤栖梧电视剧 > 第9页(第1页)
第9页(第1页)
淅淅沥沥解了内急,实在是无法把小衣理顺,只好就这么披散着衣带,再慢慢走回床上。
重躺下,刚才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经把背后伤口再挣裂,身下的被子,很快被鲜血浸透。
符潼也不吭声,由着这血流不止,身上一阵阵冷。直到再次昏了过去。
慕容鸿进来的时候,闻见这屋子里浓重的血腥味,疾步走上前,看到的就是榻上濒死的符潼,一时间,心如刀绞。
唤来了留守的太医,为符潼重上药包扎,又针灸熏艾,忙了很是一阵,总算是转危为安。
“燕国公,殿下他伤的太重,以后身边要留人,切不可再让殿下这样挪动,今次已经无事了。”
“他需要将养多久?”
“殿下刑伤过重,气海之内损伤也难以修复,至少两三个月才能恢复。而且,也不能再似常人,今后只怕,常年缠绵病榻,与药为伍。”
“知道了,有劳。”
慕容鸿听着太医的话,挥了挥手。
等其余人都退下,慕容鸿坐在符潼床边,伸手拉过他的手,手上也满满包扎着细布,隐隐透着血色。
他不敢使劲握住符潼的手,只把自己的手轻轻覆悬在符潼手上。
“我该把你怎么办?”
慕容鸿低声轻语。
符潼从小娇生惯养,从未受过皮肉之苦,如今在皇城司遭这番折磨,伤的自然比旁人还要重些。
符先一向认为守成之君,仁心为要,并不逼着符潼练功习武。可符潼心内要强,虽然比不上符先的天资高绝,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敢懈怠。
现在一身功夫,尽数毁在皇城司铁狱,身子恐怕也回不到从前。
“他一定恨极了我!”
慕容鸿暗想。
广平王催着他交出符潼,让宗人府,大理寺,皇城司三堂会审。
要务必坐实了符潼通敌叛国之罪。
可他现在这个状态,别说是提审过堂,熬刑录供。就算是稍微用力挪动,也随时会一命呜呼。
自己能护住他几时,就算几时吧。慕容鸿心里一阵疲惫和酸楚糅杂。
“若是实在护不得,阿潼,也只怪你自己命不好。”
。。。。。。。。。。。。。。。。。。。。。。。。。。。。。。。。。。。。。。。。。。。。。。。。。。。。。。。。。。。。。。
转眼间,已经月半,符潼外伤渐渐在太医悉心调理下,好了起来。
这本来就是琅琊王府,符潼自可随意在府中走动,当然想出去,却又是万万不能。
符潼试过两三次想递消息给大兄信赖的旧部,只是次次都被轻易拦截,便知这王府上下,早已经被慕容鸿打造的铁桶一般,已经不再是自己能随心所欲的地方了。
姚昶来看过他,死死的盯着他,喝了一碗茶,阴阴的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莺歌经不住自己百般哀求,出去打探了一圈,说是姚昶带走了府中的內侍领紫圭和红圭。
慕容鸿每每夜间求欢,符潼推拒不得,刚开始几次还能用自己伤重不支作为理由,后来渐渐大好,慕容鸿也就不同他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