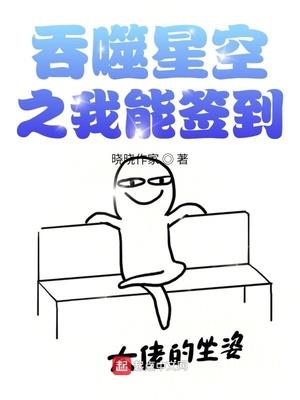69书吧>在水何方 一介行李 笔趣阁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西城更清楚定王处境,她只是担忧兄长,并不是需要安慰,果然她转开话头,“鹿鸣宴上见过状元郎一回,同他说过几句话。状元郎仁柔善感,气度雅涵,舒儿则更似冬日之阳,清冷之间又带温和。你兄妹二人性情上倒是差得远些。”
十七想了下道:“幼时便有人说我和哥哥不甚相像,连样貌也相差甚远。哥哥生得极美,我则不像个姑娘。哥哥说他幼时样貌似阿爹,现在更像阿娘一些,我大约和阿爹阿娘都像一点,只是我已记不清阿爹阿娘样貌。”
西城笑道:“状元郎生得确实极美,放榜那日,不知有多少官宦等着捉婿,听说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险些打起来,现在朝上见了,还互相吹胡子瞪眼。舒儿也是好样貌,想来你爹娘都是美貌仁善君子,否则怎会养出你兄妹这样灵秀的人来。”
她缓缓叙道:“听说陛下曾亲口褒奖状元郎才华,状元郎现下官职低了些,日后定仕途平顺。且叫你哥哥放心,你在我这里自也不差,虽不能似男子那样任官迁擢,但我公主府的人,旁人也不敢低看分毫。”
十七不会甚么谦辞,听她这样说便起身重重一礼。
西城忙拉她坐下,又与她说好一阵子话,才让清娴带她到公主府各处转转。
公主府人虽多,却并不复杂。外院有顾老管家掌事,内院由长史清娴看顾。因十七要兼左右卫,内外都要行走,清娴便带她先去探看顾老管家。
顾老管家老妻已逝,独子独孙都在上合从军,这两年6续传来消息,两人俱战死沙场,如今只独留他一人活着。他对十七甚是喜爱,说她与孙儿顾昀一般大,叹之又叹,几乎将她认作了孙儿…
探过顾老管家,清娴又带她回到内院,指高墙另一侧说:“那里便是府中校场,小娘子在校场以外是公主左卫,若公主外出,左卫随身跟随公主便可。在校场则是公主府右卫,往后右卫便在那里操练侍卫。先前公主说小娘子曾扮过男子,若在校场,还是男子身份更加便宜,右卫便假作顾老管家孙儿顾昀罢,知道顾昀战死沙场的只有寥寥几人,顾老管家也已应允,小娘子大可安心。”
十七看向高墙,似乎能听见对面兵器相撞声响。难为顾老管家献出孙儿名讳,自己无以为报,也只能代替顾昀行孝一二。
她又要到前院拜谢顾老管家,清娴笑了笑,“这府里不似其他地方那样重规矩,左卫不必时时拘礼。”
毕竟涉及顾昀,应是隐秘之事,十七便暂且放下,待日后寻个时机再行拜谢。方才西城提到甚么榜下捉婿,她不知那是何意,公主面前不好多问,又时时念之,说话时难免心神不定。
清娴见她思绪重重,问其原因。她犹豫再三才问出口,“甚么是捉婿,为何有人为之打架?”
清娴愣了下,掩口笑道:“就是一些达官显贵,家中有待字闺中的女儿,又瞧不上寻常世家子弟,定要等到殿试放榜那日,早早挤到金榜下,捉了入眼士子回家当女婿。金榜提名者多是腹有才华且大有前途的有志君子,若与那些贵人结了亲,兴许仕途也会平顺一些,很多高中士子也愿意被捉了去,两下各得其所,也算美事一桩。听说状元郎在殿试上,便得陛下赞为‘俊杰才无敌,君子艳无双。’放榜那日,早早候在贡院朱门的衣紫贵人不知凡几。好在那日状元郎未亲自去看榜,不然一个人哪里够那些个抢夺。便是现在,也有很多高官显有与状元郎结亲之意,倒未听说状元郎有应过哪家。”
十七明白过来,也跟着笑,“我哥哥自然是有许多人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世人说话多谦辞含蓄,甚至要卑微自贬。比如称自己为“鄙人”
“贱人”
,称妻为“贱内”
“糟糠之妻”
,称子为“犬子”
“不孝子”
…就是形容自己父兄要着敬语,也无不是贬低自己而抬高父兄,再加修饰溢美之词,谦虚谨慎至极。清娴头一次见到并不以极力自贬为垫石,而毫不掩饰夸赞自己家人之人。她率真坦诚,黑即黑,白即白,如今这个世道,这样的人当真少见。似乎有些明白她为何得公主喜爱,就是自己也对她生出几分亲近…
一连几日阴雨,城中低洼之处泥泞难行。魏储依站在堂前,叹息道:“本想今日带你去荷园游赏,如此大雨,竟是寸步难行。”
十七走到他身旁,张开手掌接檐下滴雨,待接满手心,再将之甩出去。如此几次,衣袖被雨水点缀斑驳,她自己并未察觉,转头与他说话,“待日后晴朗,再与哥哥同去不迟。”
这几日魏储依带她去过许多地方,买下很多物什,就差把店铺搬到家里。前日街上遇到同窗,说起荷园花开正盛,便打算带她去看一看,怎奈雨天阻路,只能待在家中。
魏储依拿来手帕给她擦手,笑她还如孩子一般淘气。怕她着凉,叫她去换件干爽衣衫。十七应了一声,转身回房换衣,返回时也给他拿件外袍。
魏储依笑道:“哥哥不冷…”
话音才落,便偏过头打了个喷嚏。十七帮他披上袍衣,面上挂着忧虑,“哥哥近期可诊过医?”
魏储依忙说:“又无病灾哪里需要看医。”
十七看着他,许久才道:“哥哥要身体康健才好。”
她一副认真模样,想必对他刚才那个喷嚏格外在意。魏储依紧紧衣襟,笑了笑,“忽觉有些凉,还是进去罢。”
午后细雨转大,十七却出门去了。魏储依以为她在房中歇息,便在书房看书,近晚时,见她从外回,惊觉她出门去了,忙迎上前,才现她身后还有一人,正是肩挎药囊的许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