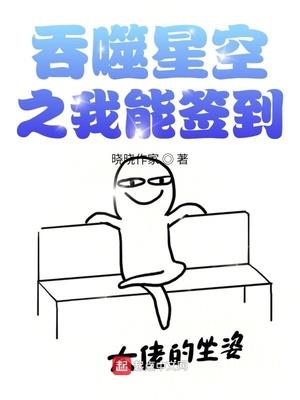69书吧>食仙主精校版 > 第577章 年关上(第2页)
第577章 年关上(第2页)
「那你说的都是年后了?」
「是,年后再调遣你。」许绰笑道,「都是壬午年的事情了。」
她掀帘上车,怀中暖炉刚好燃尽了。
「今年来旧宅里过吧,唤上些同样羁留在京的朋友,刚好可以一起。」
裴液却在车门流连了一会儿,回头看着那街上诸多的摊位,有些踌躇。
车上许绰垂眸:「你干嘛?」
「咱们不买点儿年货吗?」裴液搓了搓手,眼睛亮晶晶的。
自从见了世面丶有了钱以来,这是他过的第一个年呢。
新鲜玩意儿也太多了。
……
……
腊月廿九,一年之春将至,宫里也张灯结彩。
朱墙碧瓦结起灯笼,宫娥们将彩绸系在檐下,把乾净的雪堆成憨态可掬的小人,每年的这个时节,宫中散放补贴,乃至分批遣宫人们返家省亲,贵人们脸上也多是温笑和气,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日。
然而就在今日的紫宸殿,气氛却比一年中任何时候都要凝肃,已换上彩衣的宫人们噤若寒蝉地伏地,她们早时受皇后之命来清扫殿宇,如今跪在这里成为雕塑。
「两朝肱骨,国之叔舅……」朱衣的李翰飞甚至没有换上朝服,他跪倚在盘龙柱旁,身上还有酒气,双眼红通而麻木,唇色青紫,语声微颤,「就这麽教贼人当街割去了头颅……」
殿中杨遽虎,张梦秋,巡街之郎将尽皆跪伏,堂上却没有圣人。
是袭华美的凤袍倚坐侧,当朝皇后唇线抿得像剑,神色似淡似怔,安静地看着殿中地面,殿中静得落针可闻。
「……圣人今晨去先陵祭祀,晚些将回,我已遣人奏报了。」李凰轻声道,「事当何举,且稍待吧。」
「凰儿!」李翰飞一砸柱子,喉中痛咳,双目泛红地看着上,「叔父幼时待你我何厚!今你我遥在神京,血亲屈指可数,我堂堂西陇之李,岂能不令叔父所受之痛辱,百倍还于那贼人!你当陈情于他,令……」
「李尚书!」李凰抬眸看着他,微哑道,「殿前失仪,该当一罪。」
「……」李翰飞默然倚柱,垂下头去。
李凰安静看着地面,今日正在年关,那精心织造的华服向两边流泻,她像只凤凰般端坐在堂上,不知自己等待着什麽。
殿中一片安寂。
大约就在朝阳升起之后,金色的曦光漫进殿中,仪仗们纷纷列在殿前了,那道身影在华盖之下走入,却显然不是刚刚回宫,而是先在后殿换下了威贵的冕服,沐浴更衣之后才来到此殿。
李翰飞从盘龙柱前直起身来,双眸怔然泛红地看着这道身影,喉中哑然无言,上李凰起身跪迎,唐皇示意免礼,淡声道:「皇后也在。」
李凰今日仍然端正完整地行完了整副跪迎的礼节,站起身来,唐皇已在案前坐下。
「事我已知晓了。路上见了狄九的摺子,收了宫里的传信。」唐皇淡声道,「事无迂曲之处,案凶性恶,便遣京兆府丶大理寺丶刑部三司会审,既涉江湖,调仙人台为助,以御史季铮为监察。李故相辅国十年,是有功之臣,朕甚悲痛,凶犯若获,刑以车裂。」
李翰飞身体被殿外寒风吹得冷冷一悚,他颤着唇不知说些什麽,或者在这位圣人面前他从来没有太多开口的勇气,他抬眼看向上面旁边那道华美的身影,似乎希冀着她能说两句什麽。
这案子要查,谁能找到证据?
可这案犯是谁,难道还需要查吗?
然而没有语声,等待一晌,似乎就以这一句话结尾了,这是大唐最高规格的凶案调查组成,是一个皇帝该给的最好回应。
李翰飞僵然地退出大殿,来时根本不曾注意衣物,此时冷风令他瑟缩不止。
不必怀疑,在叔父的葬礼上,一定还会有圣人的亲笔吊词,然而他当然不会掉一滴泪……哪怕这是陪了他十年,无一事忤逆的顺相。
就如今日他如此面色平淡地说出「朕甚悲痛」,却依然是先沐浴更衣罢才来宣布这麽一句话一样。
他站得足够高,不大在乎很多事情;案情确实没什麽迂曲,他也就不投去什麽精力。
李翰飞来到神京只有三年,来到这个位置也只有两年,他见到这张威淡的面孔许多次了,但直到今天才明白叔父口中那四个字的意思。
……无情之君。
殿中安静下来,宫娥们继续开始打扫殿梁了,她们必须装作什麽也没生过的样子,在宫中做事大多时候都要是个聋哑人。
李凰低头沏好一壶茶水,唐皇已在案前翻阅今年最后的摺子,朱笔沙沙批阅着,沉静的黑眸略过一行行文字。这些奏章来自天南海北,大唐疆域辽阔,有南海的风暴,有北地的兵动。
「陛下今年想喝哪家的酒?」李凰压着微哑的嗓子,温声道,「仍去年的桃花酿吗?」
唐皇不答,先批完了手上摺子,道:「那日你说摘星楼的新酒……」
「是【新雪】。」
「嗯,今日尝了些,尚好,多买些来吧。」唐皇平日不怎麽饮酒,偶尔只品其味,但年关总与宫人相敬两杯,或者招待使节宾客。
「好。」李凰温温一笑,「另,明日有南国使团来,陛下穿哪件冕服?」
「皇后选吧。」男人不大在意,也没什麽多馀的话。
「遵陛下令。」上带着笑,衣服也与平日不是一个色调,整体变得乾净而新,而且多有些鲜艳的颜色。
街道两边的摊位也随着温暖起来的阳光纷纷搭好了,多挂着朱红的彩画,风中摇摆的春联,还有各色甜食与令孩子们蹦跳凝望的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