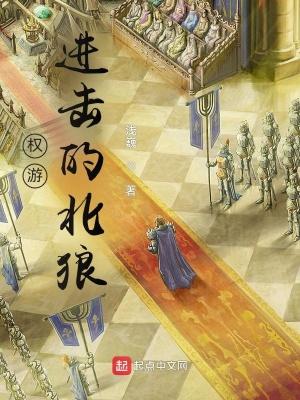69书吧>围屋故事 > 第48章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第2页)
第48章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第2页)
“是的,婆婆。”
陈安澜迅速回答。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妹子吧!”
老婆婆似问非问,然后转身进去了。
陈万福的老婆整理好了房间,在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稻草,然后客气地说:“你们男人就打地铺吧!我们女人和孩子睡床铺。”
说完咧嘴一笑。
“我们也是男人,就和爸爸一起睡地铺吧!”
几个小男孩倒了下去连翻了几个滚。
“不行,你们人太多了,挤不下,分几个孩子跟我睡。”
老妇人笑呵呵地说。但孩子们似乎都不答应。
他们两家的人缘情谊源于那次超历史的洪灾。那场洪灾淹没了众多村庄,那地势较高的围屋就成了临时避难所。每家每户都挤满了人,从大坪到小巷子,没有一处空地。陈安澜收留了陈万福一家,是因为同情他们家老弱病残,特别是那位生病发高烧的老妇人。陈安澜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为她抓药、熬药、端茶倒水,无微不至地照顾。
这次是陈万福亲自向族长请求,希望安排陈安澜一家住在这里,这个提议最初是由老妇人提出的。
那天,老妇人听说族裔祠堂正在开会,讨论如何安置围屋的难民。她突然想起了早年在围屋避难时,陈安澜像儿子一样细心照料她。那时,陈安澜还是单身,两个儿子年幼,老母亲卧病在床。
“弟妹,我们一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尽管族亲真诚相待,生活上也照顾周到,陈安澜一家却感到越来越不安,尤其是那位外地嫁入的高淑珍,她天性善良,容易感动,经常真诚地表达感激之情。
“我们明天开始帮万福弟做农活吧!”
高淑珍向丈夫提议。
“不用了,现在是农闲时节,我们自己也闲着呢。”
陈万福微笑着回答。在农村,哪有真正闲着的时候呢?到了田间地头,总能找到活儿干。他这么说,不过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贤弟,我们也是种地的,闲不下来。虽然我们不如弟弟和弟妹能干,但去田里做些粗活是可以的,我们还能从你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陈安澜也笑着回应。
第二天,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孩子们见大人不在家,便放肆起来。他们下河摸鱼,去池塘钓青蛙……随心所欲,像一群无人看管的野孩子。
中午时分,孩子们满身泥泞,湿漉漉地回来了。大人们只是轻声责备几句,并未过分苛责。毕竟在农村,孩子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衣服弄脏、皮肤划破是常有的事。但他们的努力也有所回报,小鱼篓里装满了小鱼,草绳上拴着几只还在鼓腮的青蛙。
陈万福的大儿子十二岁,身材伟岸,肤色古铜,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犹如希腊的雕塑,幽暗深邃的眸子,显得狂野不拘。他也是围屋私塾的学童,学堂被毁先生无家可归,二十几个学生只好在家呆着,无所事事总天凑在一起玩耍。
下午,大人要下地干活,陈万福嘱咐孩子们不要走远。他的大儿子哪能听话,现在不要上学正是玩耍的时候。
“我们上午下河摸鱼,下午上山捕鸟怎么样?”
大个子提议道。
“可以,就是没有捕鸟的工具。”
有人说。
“我家有几把鸟卡子①,不知道线绳子有没有断掉。”
邻居小孩说,我这就跑回去看看。
一会儿,那小孩手上拿着五六把鸟卡子兴冲冲地回来了。
大个子接过捕鸟具逐个检查一番,点了点头说:“嗯!还行,绳子还有韧性,可以用。”
“用什么做诱饵呢?”
是啊,诱饵是有讲究的,有的鸟爱吃虫子,有的鸟爱吃粮食。
“我们要就捕大鸟,那些小鸟不过瘾。”
有个小孩贪心十足,巴不得捕几只一斤多重的鸟,让几家人都能喝上一口营养美味的鸟汤。
“好吧!那大家就去找虫子吧。”
最易得的是蚯蚓了,还有就是土蠕虫,用锄头在阴湿的泥土就能挖出来。
这些都具备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上山了。殊不知,山上的鸟大多在树上活动,以果实为食,很少飞到地上觅食。小孩子不懂常识是情理之中,一无所获也无所谓,毕竟是凑在一起玩耍而已。
几个小孩看准了下诱饵的点,那是鸟儿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有许多梅沙果树,现在已经过季节,树枝上还残留一些小果蒂。
几只小鸟飞过来,落在树枝上戏耍。一个小孩拿出弹弓就要开打,旁边有人劝阻:“别,别!不要惊动了鸟,要不然我们就白费功夫了。”
那个小孩瘪了瘪嘴,把弹弓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