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书吧>一梦金陵齐溪 > 第78页(第1页)
第78页(第1页)
见他左眼眼角乌青一片,她早就吓了一跳,哪里还有心情说笑,&1dquo;王爷怎么这般不小心呢,一会儿不见怎么就受伤了,到底怎么磕碰到的?”
&1dquo;你别担心,”他口气无关痛痒的道,&1dquo;爷们儿们一起练布库,偶尔会有擦伤在所难免,谁下的重手,我也没让他好过,这不刚上过药么,没什么大碍的。”
念瑭这才放心下来,高严送走大夫上楼来了,立在外头扣门框,&1dquo;卑职叫了些吃的上来,您二位先垫垫肚子,什么时候出,等王爷您的话。”
话说着,客栈的伙计端了饭菜进门,祝兖吩咐高严道:&1dquo;你先去集合人马,等下准点儿了就出。”
两人用过早膳下楼走到客栈外,何祎走上前道:&1dquo;高严已经带着王府的兵马已经在城门处等候了,请王爷移步吧。”
念瑭现他的左眼周围也挂了彩,还有药水擦拭过的痕迹,她甚觉诧异,心说这俩人的伤不会是互相给打的吧?按理说只是摔跤相互切磋的话,未免下手也太过重了。
&1dquo;你怎么也受伤了。”她关切的问道。
何祎抬起头,扬唇轻笑,&1dquo;姑娘不用担心,爷们儿们之间较量,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力道大了,相互给些苦头吃很常见。”
竟然连说辞都如出一辙,念瑭心里产生了狐疑,不待她深究,祝兖拽起她的手腕,冷冷撂下一句话,&1dquo;谁担心你了?闲没事儿可甭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她被他带着往前走,回头看见何祎立在原地一动不动,祝兖的步子又加快了,&1dquo;你瞧他做什么?他有我好看吗?”
念瑭不明白这闹得是哪出,她啼笑皆非的问,&1dquo;王爷您跟何祎有什么过节吗?干嘛要给人家甩脸子?这次要不是因为他,我还见不着您呢。”
&1dquo;我已经跟他道过谢了,这小子不识相儿,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念瑭听了这话噗嗤一下笑了起来,他侧过头看她,诧异的问:&1dquo;你笑什么呢?”
她笑着摇摇头,&1dquo;王爷这个样子真像个小孩子,跟人家打架打蹭了,竟然赌起气来了。”
有侍卫牵了马过来,祝兖接过辔策扶她上马,细心帮她拉展袍角,&1dquo;现在嫌弃我幼稚也晚了,往后余生,就请砚砚您多包涵了。”
活落他也拉了匹马,翻身坐了上去,两人相视而笑,不约而同的朝前方望去,视野里层层尽染初春的绿,往后余生,就这般相携而走吧。
回京的脚程并没有刻意走的有多快,念瑭沿途由棉袍换成了单衣,脸畔鬓角的装饰也由梨花海棠,变成了蔷薇牡丹,全都是停歇时,睿亲王亲手采摘为她插戴的。
真正回到京城之后,已经到了四月中旬,侍卫中自然有人打了前哨前去通风报信,所以到达睿亲王府门前,早有乌泱一大群人前来相迎。
下马的时候念瑭耳鸣起来,眼前混苍苍的有些站立不稳,祝兖注意到她的不适,上前扶住她问:&1dquo;是不是又头晕了?路上就早说要请大夫来瞧的,你偏要逞强。正是换季的时候,兴许是着了凉,你先回衍井斋歇着。”
他抽下汗巾擦她额头的虚汗,念瑭接下来,勉力笑了笑催促道:&1dquo;我没事,王爷您先去忙吧,这么些天不着家,别让太福晋等急了。”
常禄见状早已走了过来,先冲睿亲王打了个千儿,又道:&1dquo;王爷您先回银安殿问安吧,念瑭姑娘这边奴才先帮您照应着。”
祝兖这才放下心,在众人的簇拥下先到了银安殿,跟他的预想中的场景类同,像他之前出远门一样,归家后母子相见,互诉一番思念,聊些家常。
谈到唐家的案子,虽然官方话是说豫亲王是因抗匪战死德州的,不过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内里的真相后来就已经传遍宗室,朝堂内外不过是共同维护豫亲王冠冕堂皇的死因罢了。
太福晋道:&1dquo;我到现在还心存后怕,你不该瞒着额涅的,早知这趟外差如此凶险,咱们王府上该做万全之策才是。罢罢!好在事情都过去了,不提这茬儿了。”
提到念瑭,太福晋眼角略微有些湿润,&1dquo;没想到这孩子身世这样曲折,心眼儿也是实的,当时求着我非要同何二爷一起去山东去找你,这一来一回这么远的路,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你们俩可真是一条藤上的锯嘴葫芦,给我捂了个严严实实,得亏万岁爷开明,否则真出了什么事儿,额娘这心里该有多淹心呐。”
听太福晋的话音对念瑭的评价多有偏袒,祝兖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道:&1dquo;有件事儿儿子请额涅一个恩准,您瞧儿子岁数也不小了,是该。。。。。。”
知儿莫若母,她这当母亲的要是再猜不出儿子什么打算才怪,&1dquo;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太福晋堵住了他的话头,见他张口还要争辩,沉沉叹了口气道:&1dquo;允璟啊!你当阿玛了知不知道?!”
他听了缓缓扣上了茶盖,眉眼间大雾茫然,一瞧这个神儿,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太福晋脸上笑意满满,&1dquo;收生婆婆们在家里守了十天十夜,前儿晚上生的,是个儿子。”
&1dquo;怎。。。。。。怎么没人提前告诉我?”祝兖略做回忆,仔细算了算,的确足月了,只是他忙起来完全被占据了心神,竟然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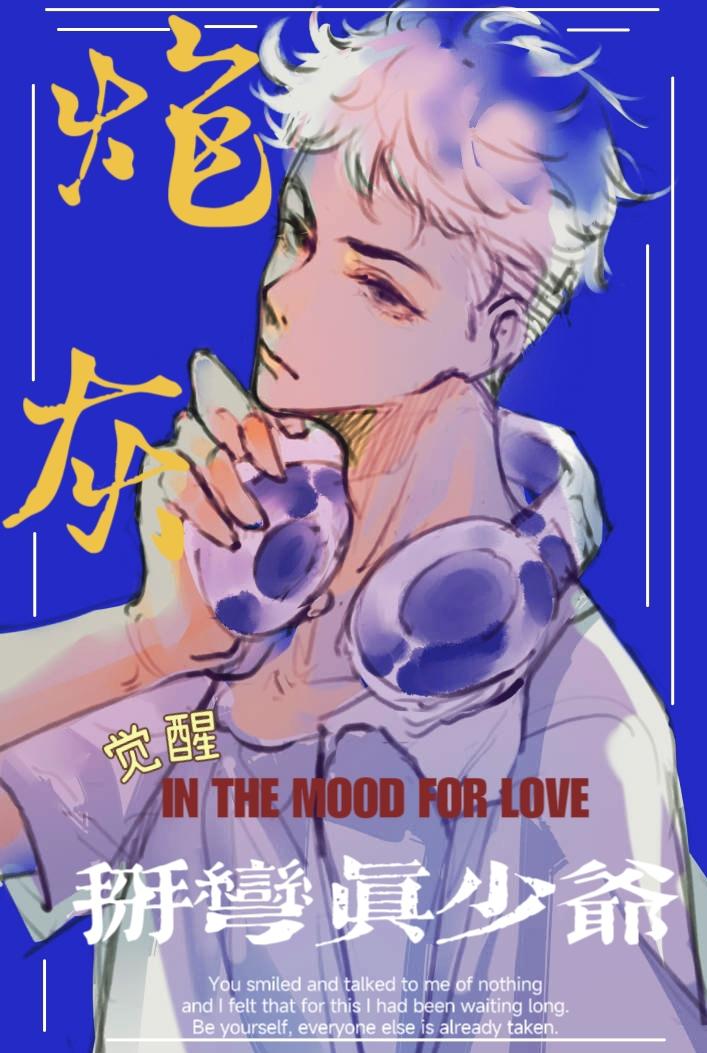
![[综英美]跟着红桶学做人](/img/1784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