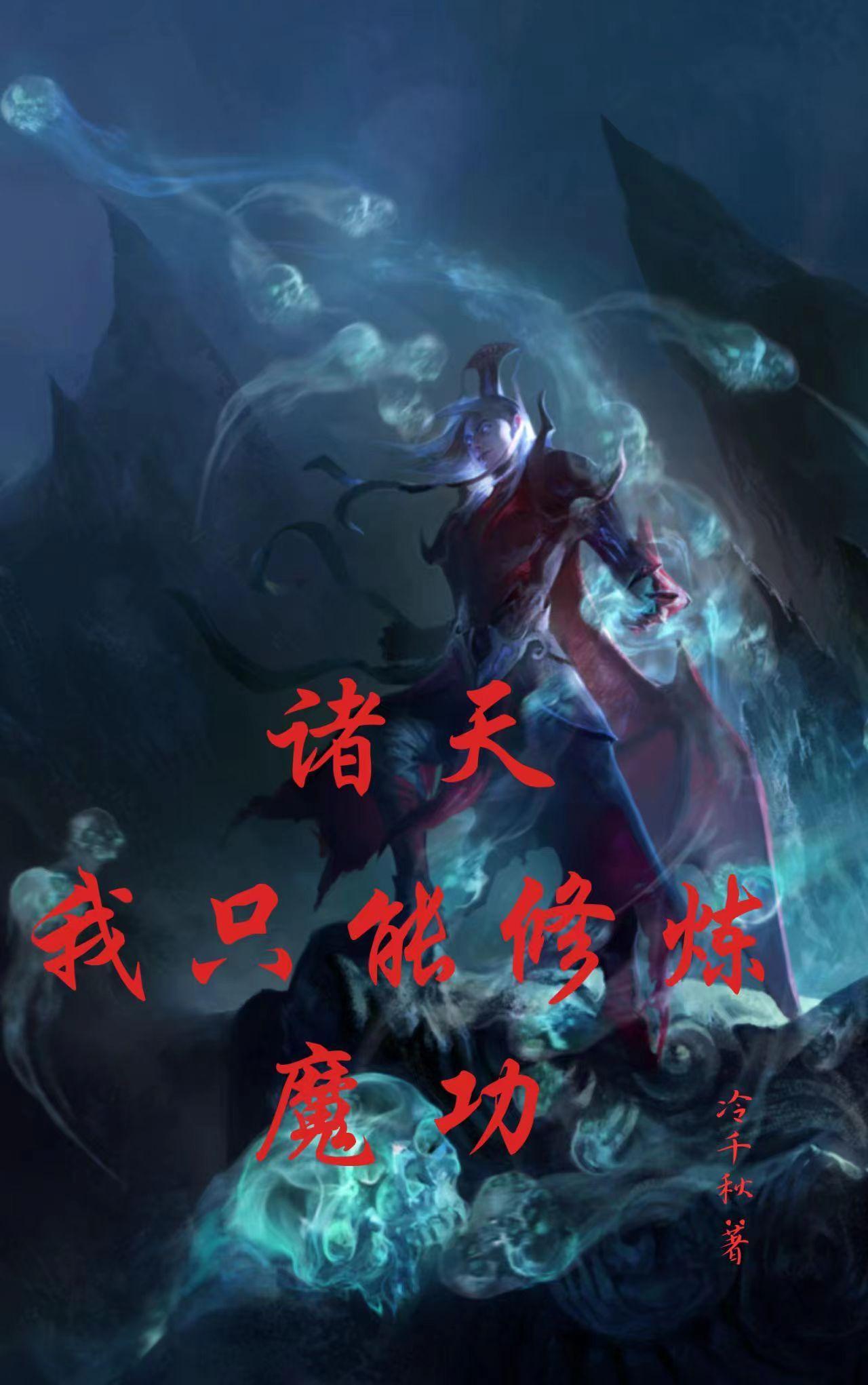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名裱 番外 > 第2页(第1页)
第2页(第1页)
原本他小时候在国画上极有天赋,也正因如此,曾短暂地获得过舒国华的欢心。
然而在受伤之后,他的右手拿不稳毛,不得不放弃国画,改画油画,因为油画只需要拇指和食指就能握住杆。
现在的舒青末是华南美院油画专业的大学生,不过背地里,他一直在用左手练习工画(注),水平早已过了当年。
右手画油画,左手画国画,这是舒青末的特长,也是他的秘密。
所以准确来说,此时此刻在窗边的画案前,舒青末用左手拿起了毛。
宣纸上很快出现了几根墨色铁线,传神地勾勒出姿态夸张的黄袍道士。
舒青末熟练地运用手中的狼毫细,用点画的手法突出黄袍上的重点,接着再细画出道士手中的招魂铃。
而就在舒青末画得正起劲时,他左手边斜对面的窗户忽地被人推开,一个手拿香烟和打火机,满脸烦躁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眼前。
裱房的位置位于整栋建筑的角落,如果把这部分角落看作大写字母“1”
,那竖线的地方是长长的走廊,而横线的地方就是裱房所在。
舒青末能看清斜对面男人的一举一动,反过来说,那个男人也能看清他正在画画。
舒青末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放下了手中的毛,有意思的是,对方也条件反射般地收起了不耐烦的神情和手中的香烟。
除去那西装挺的身姿和朗目星眉的面庞,舒青末对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一定很善于伪装。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身上的气质便判若两人。
“你好。”
阎宗琅率先开口,对舒青末微微颔。他的语调从容沉稳,眼神扫过窗框后的画案,接着又回到了舒青末的脸上。
“你好。”
舒青末礼貌地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把手边的毛推远了一些。
按照当地的葬礼习俗,亲属佩戴黑色袖章,客人佩戴白色袖章。
舒青末看到对方胳膊上戴着和他同样的黑布,怀疑这人是舒家的远房亲戚。因为若是熟悉这座宅子的人,应当不会来这个角落抽烟。
他好心提醒道:“你回到刚才上楼的地方,右转走到底有一个露天阳台,可以去那里透风。”
阎宗琅顺着舒青末的话回头看了看来时的方向,接着对舒青末道了声“谢谢”
,关上走廊的窗户转身离去。
楼下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震得舒青末耳膜都在麻。
院落里弥漫起青烟,浓浓的火药味飘到二楼,无论是听觉、视觉还是嗅觉,都让舒青末极度不适。
他本想关上裱房的窗户,但又不想被楼下的人看见,最后只得用右手掩住了口鼻。
他重拿起毛,在道士的脑袋上画了一副耳机,又在他脸上画了一个口罩,无聊地心想为什么他不是神马良,画什么都能变成实物。
好半晌后,鞭炮声终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