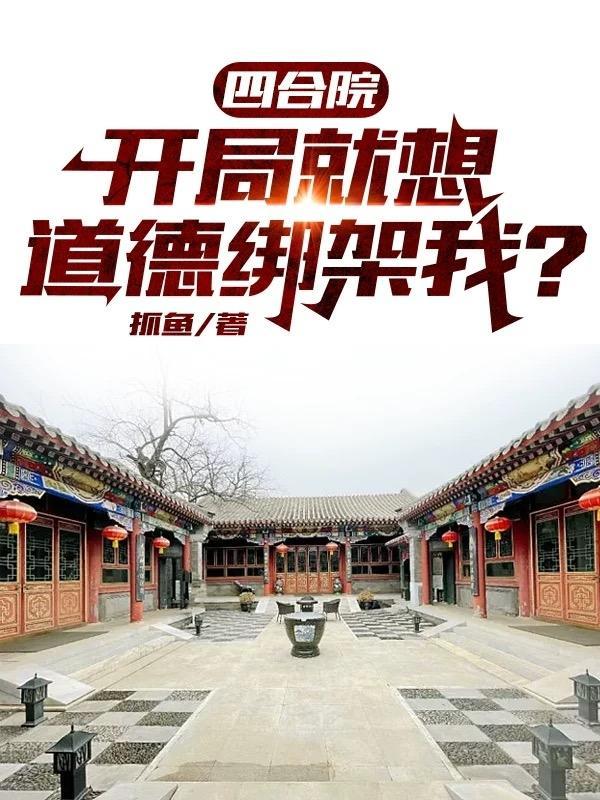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重生后太子妃罢休了 > 第88頁(第1页)
第88頁(第1页)
天已漸漸擦黑,燈火見亮,連著三日都未好好洗漱的阮瑤清,待清洗好後?,忍不?出輕鬆了口氣,邊絞著微濕的頭髮邊出了耳房,只是待看見屋內的人,她不?禁頓下了腳步,面上又燃起了疏離冷冷道:「天色不?早了,殿下還有何事要找三娘,若是無?甚大事,可否先讓三娘歇息。」
徐元白倒了杯茶給她,邊示意她坐下邊道;「三娘可是搞錯了?」
「什麼地方錯了?」阮瑤清拉緊了中?衣衣領問道。
徐元白輕笑了一聲,一雙深潭似的眼睛笑意盈盈的看著她道:「你我如今是「夫妻」,夫君歇在娘子屋內,實在是天經地義,哪有像你這般趕人的道理。」
阮瑤清皺眉答道:「那都是假的啊!」
徐元白點了點頭:「確實是假的,可目下是在旁人的眼皮底下,唯恐被人瞧出端倪,還需得辛苦你一直陪孤演戲才是」他眉眼一挑,又輕「噓」了一聲才道:「如今你我在旁人的地盤上,還是要當心些才是,你還需多適應適應才是,孤不?禁現在會在此,夜裡也會在你這處歇下。」
「那也不?必同寢!」阮瑤清幾乎要被逼的理智失去,啞著嗓子駁斥道。
徐元白卻恍若不?覺她的怒意,仍舊嬉笑這點了點頭:「自然是需要的,怎麼?孤說的你竟是不?信?」
自然是不?信!也是懶得在搭理他,起身?便要將?他趕出去。
方才還嬉笑著的徐元白,忽的面色一沉道:「你方才不?是問孤,汪則口中?的韓老?爺是何人嗎?」
阮瑤清聞言手募自頓下,怎好端端的又說起姓韓的來?
見他神色嚴肅,阮瑤清也不?再動作,只是靜等著他說話。
「這韓老?爺可是尋南最大的商賈,你可知道在一年前?,此人毫無?名聲,不?過短短一年便發展至此,以至於百里之內,無?人可睥睨。」徐元白頓了一下問道:「你猜猜他到底做的是什麼樣的生意?」
阮瑤清未言,只是搖了搖頭。
「綢緞,瓷器,糧食,但凡掙錢的整個南尋,遍布都是他的產業。」
阮瑤清皺眉道:「這聽來倒也算是正常。」
徐元白輕笑了一聲道:「這些聽著倒是正常,但其中?還有一樣。你大約絕對想不?到的。」
「是軍火?還是私鹽?」阮瑤清漠然出聲問他。
徐元白聞言倒是吃了一驚,眼裡閃過一道光華問她:「你怎知道的?」
阮瑤卿聳了聳肩頭道:「能讓太子殿下微服私訪親自探案的,左不?過是這兩個原因。」
徐元白不?禁有些讚賞的點了點頭:「孤收到的消息,這韓昱兩樣都沾,兩樣都犯,不?得不?說這韓昱的膽子與胃口,可不?是一般的大。」
這下就連阮瑤清都有一些吃驚了,不?禁問道:「殿下可是發現其中?有什麼不?尋常的牽扯?」
徐元白點了點頭,正要說話,門被輕聲敲響。
進來的正是匆匆歸來的祿二,他看了眼阮瑤清,見徐元白不?甚在意,便跪拜在地道:「果如殿下所?言,這汪則進入韓府之後?,不?過半個時辰的時間便從角門出來,屬下跟著他走了一道,親眼見著他進了府衙的門,屬下一直等到直到日落西山也沒?見他出來過。」
徐元白聞言毫無?意外?,眼睛微微一眯道:「果然如此。」
又看向阮瑤清:「你放才不?是問其中?有什麼牽扯嗎?這便是牽扯,孤倒要看看王邢之到底是哪來這樣大的膽子,是朝廷發的俸祿不?夠,還是他貪心不?足。父母官不?為百姓所?想,百姓所?勞,竟是與商賈勾結一處!」
阮瑤清聽的明明白白,他話語中?的氣氛與失落,不?禁嘆了口氣,對著一旁的祿二:「你先下去吧。」
祿二有一些不?放心的看了眼徐元白,才點頭應是退了下去。
直到祿二退出去,徐元白人仍舊坐在那處,雖一言不?發,卻似歇斯底里即將?而來的暴風雨,阮瑤清未在打擾他,而是走到了床榻邊坐下,與他拉開了距離才道:「殿下是何打算?這樣的蛀蟲,如何拔除乾淨?蛀蟲既有,扒出了就是,倒不?必為此苦惱些什麼。」
徐元白這才被分了神,見她此刻正乖巧的坐在床榻上,眼裡滿是擔憂之色,心不?禁一暖,他忽然明白為何前?世自己?會與她如此恩愛,她卻是個蕙質蘭心極懂他,心疼他的女子。
徐元白有些疲累的笑了笑,唯恐她跟著自己?操心,不?在意道:「倒也不?是什麼難事,交由孤來便是,時候不?早了,早些安歇吧,你莫要操心才是。」
阮瑤清自然不?操心,她聳了聳肩表示瞭然,見他從那副可怕的脾氣里抽離出來,便不?再怕什麼了,這徐元白一旦似方才那般,便似失控的狼虎一般,脾氣安耐不?住一發不?可收拾,若不?是擔憂會牽怒到自己?或者旁人,她才不?至於去開解他。
夜漸漸深,屋內燈火漸滅,阮瑤清連著三四日都未睡踏實過,此刻已經困頓的不?行?,可這屋內僅且只有一個床榻,她不?禁有些犯難。」
可讓她跟那狗太子同床共榻,倒不?如殺了她好,她四處看了一眼,最後?將?目光落在了一旁的軟塌上,她的目光在床榻與軟塌只見來回看了幾眼,最終只得無?奈的抱著軟被走向額軟塌。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