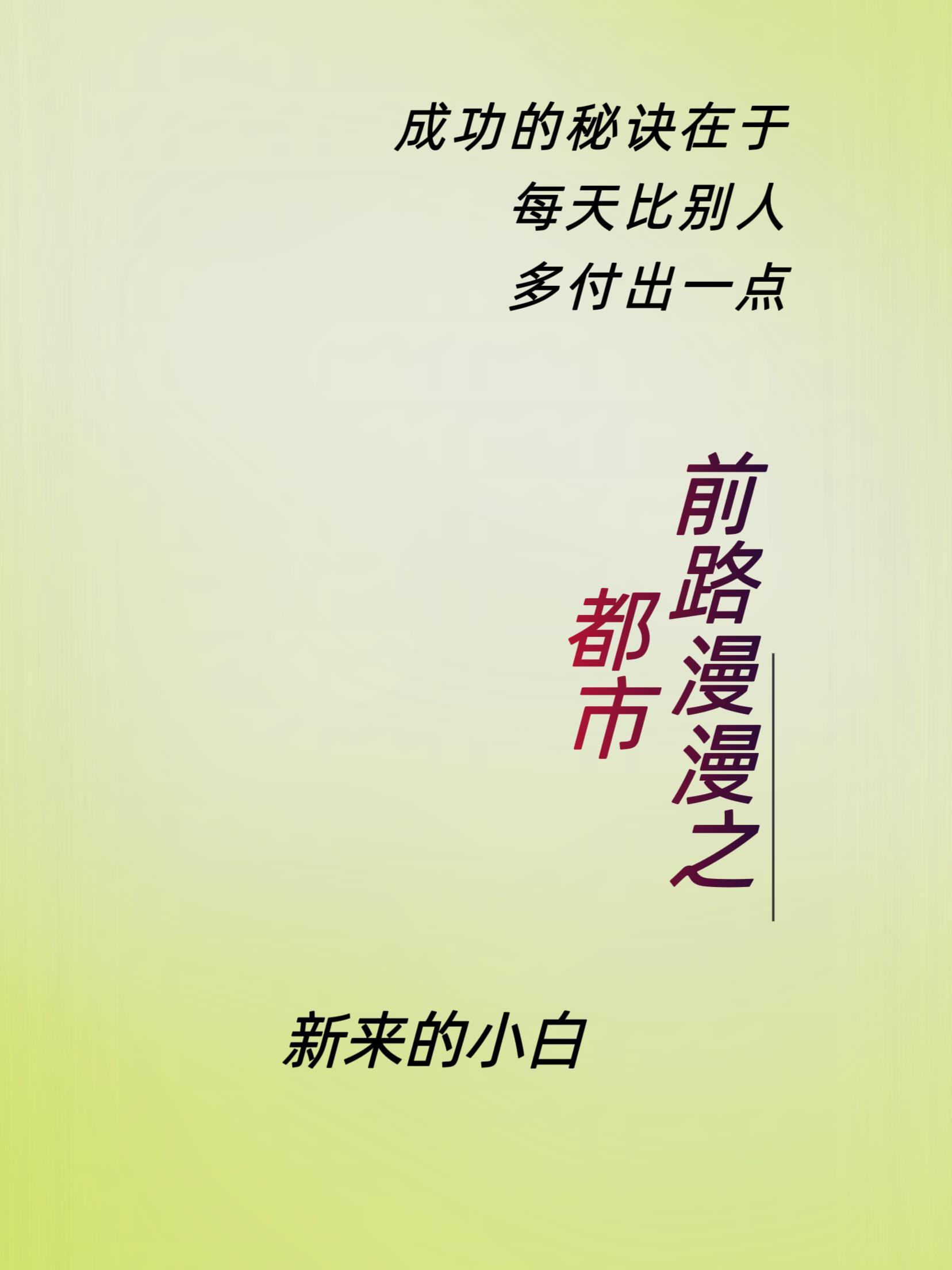69书吧>卿本包袱全文阅读 > 第130章(第1页)
第130章(第1页)
疼痛在伤口处尽情肆虐,冷汗在额前起了整整一片,我的下唇几乎要被我咬出血来。
不行,得忍住……
我在伤口处摁了几下,这才摸到一个硬结,我抽了口气,提起匕首在那块地方用力一剜。我终于禁不住地喊出声来,那种撕裂般的痛楚深入心扉,像在身体里窜涌的毒液,顺着血液蔓延到身体各处然后麻痹我的每一寸知觉。
我瘫坐在地上,眼泪和汗水参杂在一起,流进我的嘴里,溢出苦涩的咸腥味道。
如果经此一劫,这所谓的“神血”
还没办法恢复……我就拿着匕首去划凤七蛤蟆的手,他奶奶个熊的谁让他诓我!疼死老娘了!
过了不一会儿,我的眼睛开始变得异样。原本我的眼睛只能收进一些朦胧的光线,分辨不出人影轮廓,只能瞄见模糊成片的虚影,所以除了辨别天色和光源,其他的一概看不见。如今……我眯了眯眼,竟能大致描摹出一定的线条来……
至少,家里的窗口和桌台,我已然能隐约看出个全貌来了……
渐渐地,我的伤口开始从麻木变成了剧烈的疼痛,不多久,就连疼痛也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皮肉一丝一丝渐渐连结在一起的神奇感觉。
猛然间,静默了许久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重新奔腾起来,就像被强行摁下去的蛇头,再次张扬起了充满力量的红芯。我能感觉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我身体里缓缓复苏,如同黑夜里突然开合的双目,在束缚开解的一瞬迸发出妖娆而诡谲的浮光掠影。
我垂头去看自己的手,上面的红色越来越清晰,直到整个伤口,整个手腕都完整无缺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那抹妖冶的红,像一根摇晃的飘带,捆绑着我的思绪,将所有懵懂和遗忘,一朝破灭……
我想起来了……
我是……沈世怜……
若不是被窗缝中泄进来的阳光打了眼,我抬手遮挡时手腕上的血滴到了我的脸上,我恐怕早忘了还有阿朗需要我去解救。
我拍了拍脑门,一下子蹦起来,扑到阿朗跟前,然后微微一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
他皮肤黝黑,方方的脸和英挺的鼻子,眼底,有一条浅淡的疤痕,但他看起来依旧很憨厚老实。他整个人如我想象的那样精瘦,他的衣裳是凤巢宫里的侍生服,若换做他平日里下田着的粗布麻衣,那大概便与我臆想中他的模样分毫不差了。
我毫不犹豫地将匕首拿过来,顺着刚刚切口没完全愈合的地方再度划了划,立马便涌出了一股艳红的血液。我将血滴在他的嘴里,然后抬起他的下颌,看到他下咽的动作后,终于松了一口气。
半晌后,他的脸色开始慢慢恢复,手也渐渐回了温。
我去湖边打了水,谁知刚好碰到小田妞,她抱着一缸水从我旁边走过,正有板有眼地训斥她那贪玩的小妹,声音之聒噪尖锐非常好识别。看到我时她一脸的惊讶,我看到她时也小小地讶异了一番,然后挑了挑眉,默默感叹一句:好大的胸。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估计再放一个大扇贝才抵得上她的高度和阔度。糟心,现在的孩子都发育得那么好么?
她指着我咿咿呀呀了半晌,吐了一句:“你你你你看得见了?!”
我无心跟她计较那么许多,走过去一把拉过她,她吓得连忙大喊救命,我嘘了一声,“带你去见心上人而已,喊个屁。”
小田妞被我一路拉到了阿朗家,她原本挣扎着不要不要,结果看到阿朗后双眼放光,一个箭步扑到了阿朗跟前,痛哭流涕地说着原来你还活着。
恰时阿朗醒了过来,他费力地睁着双眼,看了看小田妞,笑了起来,再看向我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莫名疑惑的样子,问道:“……她是谁?”
小田妞傻眼了,回头看了看我,“你不记得了?”
阿朗艰难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一丝意外。因为我血刚恢复,血中还有残存的吟月霜香,那毒性大,如今入了他的身,他不记得我我也能理解。唉,这般看来,我和他注定是没有缘分的。
我砸吧砸吧嘴,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小田妞便追出来问我要去哪儿。我摆了摆手,说:“以后他是你的了,办喜酒的时候我会来,你对他不好的话,我就棒打鸳鸯。”
说完觉得不过瘾,我连忙再加了一句:“别家暴啊。”
她仍是不依不挠的问我要去哪儿,我无奈,只好告诉她,我要回家。
后来也不知是不是我幻听,走得快看不见她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一句“对不起”
。
耳朵太灵敏,倒也是有好处的。
当我走到凤巢宫的宫门前时,已快入夜了,好吧请原谅我依旧差得没边的方向感,这原本走一个时辰便到达的地方硬生生被我拉长了四倍,绝症不好治啊。
我望了望天边逐渐暗下去天光,莫名的兴奋从心底澎涌而出。兴奋是为什么呢?如今我能想到的最靠谱的理由大概是,啊,小凤仙的真面目终于要揭开了,不枉老娘辛辛苦苦瞎了一段日子!
至于为什么不害怕那些埋伏在黑暗中蠢蠢欲动的渣滓们……我琢磨着,也许是某种“我百毒不侵你奈我何?”
的犯贱心理作祟。
毒呗毒呗,反正你们毒不死我!小凤仙,老娘来保护你,让暴风雨来得更荡漾些吧!
不过一想起小凤仙……我还真是有些心虚……唉,不说了,说多了我和他都是泪。
刚与看门的猎头们报备过后,小潭便匆匆赶过来了,她奔到我跟前时,喘了好几口气,说道:“姑娘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得过好些天才回来……甚至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