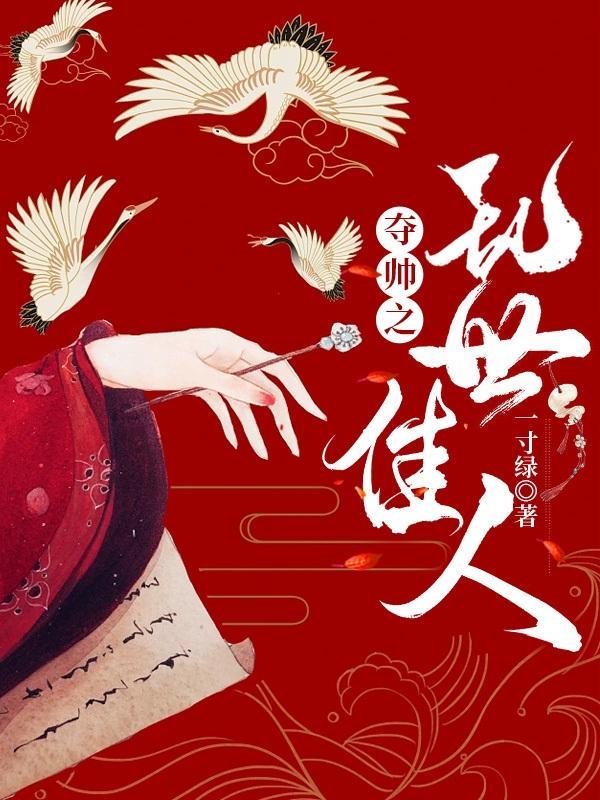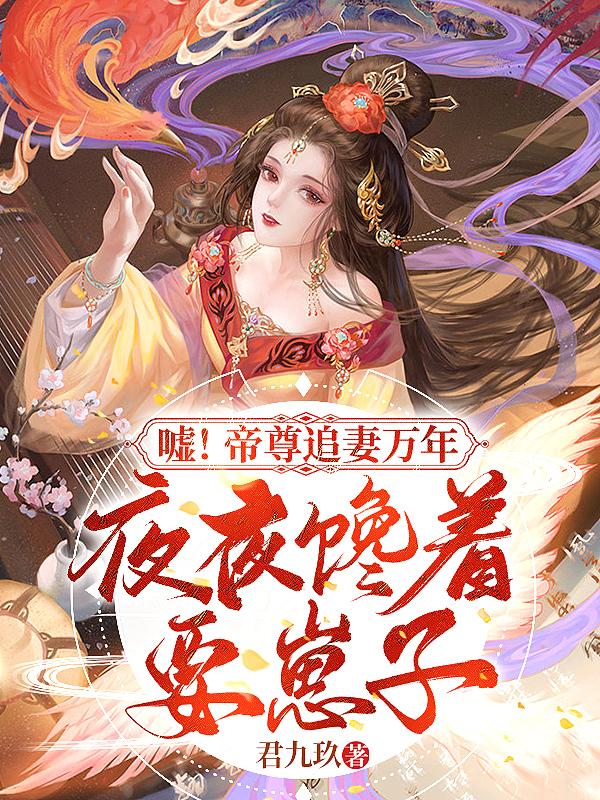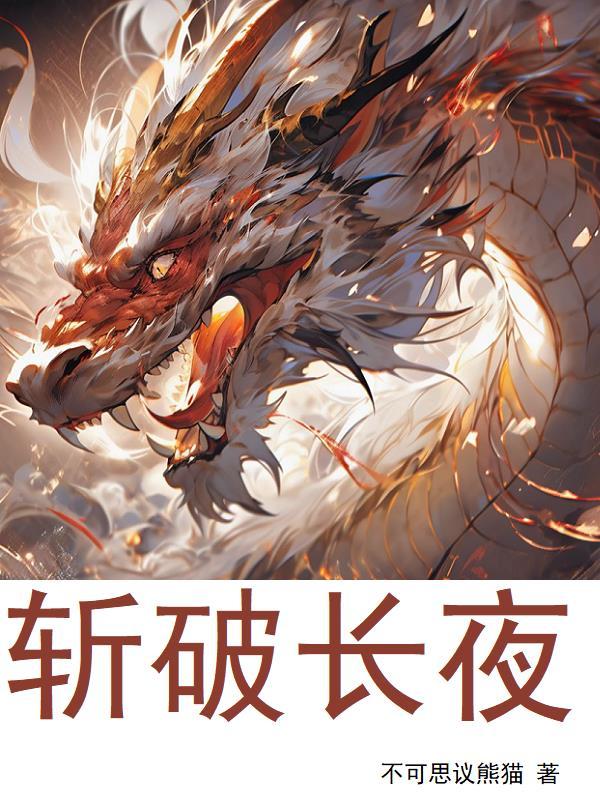69书吧>长生传剧透 > 第3页(第2页)
第3页(第2页)
“置良吏,免税赋,徐徐调治,终会万民所向。”
“若我们仍是败了,你说,会如何……”
“万民唾弃,遗臭千年。”
“若胜,又当如何?”
“呵,”
顾长生轻笑起来,“力挽狂澜,救我军于水火之中,此乃不世功勋——十三,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所书写。”
“……我明白了……”
顿了顿,又问,“……何时启程?”
“即刻。”
“你带多少兵马?”
“一万五千。”
“太少了。”
“此战重在快捷。——十三,我们必须争取时间,瞒住所有人啊。此去我直取高车,随后夺其良驹,以壮骑兵。高车平,我便奔赴南其,你可在南其边境布下兵士与我会合。会合后,我便一举攻下南其,再赶回与你大军会师。”
夏侯日月深思道,“我令铁甲骑在南其与你会合。”
“不可!”
顾长生断然拒绝道,“铁甲骑,乃如今我们手上仅有精锐。不可轻易动用。”
此次平柔然,夏侯日月手上兵力最多,有六万之众,然,其中四万五千人尽皆新兵。到军营后,身为宁远将军的顾长生一熟悉营中事务后,当机立断,即刻整顿兵力,将部分老兵抽出组建精锐铁甲骑,其余的老兵则统统分配到各部,任长史、兵曹、队正等中下级将领,统领新兵。而新老兵一混编,战斗力自然下降,所幸虽然兵力薄弱低下,但军中武器精良,补给充分,更有由明教教众所组成的精密情报网。“但你就这么带着一大群新兵出战,我如何放得下心来?仅凭这些连血也没见过的新兵,又如何能够一举拿下高车,再夺南其?”
顾长生傲然一笑,“这有何难?我会在行军途中演练兵士,以战养战。几场仗打下来,新兵们全成了老兵。再许以破敌后的钱财女人,何愁不成为虎狼之师?区区高车南其,又何足挂齿?!”
夏侯日月沉声道,“长生,骄兵必败。”
顾长生正色道,“此乃谋定而后动。顾长生绝非莽撞无脑之人。”
“谋定而后动?那为何不先取南其,再夺高车?”
要知道,南其富饶,而其战斗力向来不如高车、柔然。“南其性怯懦,只要我等破高车,何愁南其不臣服?”
顾长生详细解释道,“高车之力的确远较南其为强,先取高车是为立威,也为练兵。兵士只有跟强硬的对手较量,方能成长。南其人生性狡猾而懦弱,只看当年天朝大军所至,赶不尽的投降就可知。当我们以雷霆手段破高车后,南其人会害怕。在我们军队压境之时,南其人纵不会立即举手投降,但抵抗力亦会大为减弱。若我们再在南其境内以暴烈手段对敌,南其人最终只会选择投降——如此,纵然战高车时会费些功夫,但南其却可迅速拿下。——若换转过来,则不易为之啊。”
“……”
夏侯日月细细思考着计划的可行性,不发一言。顾长生继续道,“取高车,重在以战逐渐练出精兵;而夺南其,是在与你所援的军队会合后,重在人多势重,再配上高车这前车之鉴,南其必会自降。”
夏侯日月一直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很久过后,他终于认可了,“你,自己小心。”
“你也小心。”
语毕,顾长生便头也不回的踏出了帐门……惘惘看着顾长生远去的身影,夏侯日月心中茫然:在上官清明死后,长生,似乎改变了很多……这,究竟是种改变?亦或是他的本性如此——只是在昔日里,隐藏了……摇摇头,夏侯日月将疑问略过不想,踱至沙盘旁,继续专注于战局……柔然乱,王随高宗出征。高宗恩宠优渥,远超侪等。时魏国公拟订四围合以歼敌之策。令高宗深入柔然,破贺兰后直奔雁门,以成四合之势。王虑此策虽佳,然途遥意难合,柔然勇悍,必于会师前破雁门。王知事不可为,遂向高宗进言:贺兰集精兵,马壮兵强,正面相触,必不可挡其势,徒折兵力耳。然高车南其郡内兵力空虚,愿自率轻骑奔袭高车直取南其,剪敌之羽翼,如此,何愁敌之不破?高宗深以为然,翻然改图,因机立策。于是分趋而往,高宗领大军随原令镇遏,王率轻骑相机而行。——《天朝史·亮王本纪》自中州与夏侯日月分师后,顾长生领着军队一路奔赴高车。急行军时,他将所有部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前卫,负责派斥侯在前方侦察。第二部为中卫,分别派人在左右两翼侦察。第三部为后卫,负责派斥侯在后方侦察。如此,组成一个防守严密的军团。大军很快行至高车境内。一入高车境内,顾长生便停下急进的脚步,重整大军。他将整支军队分为十支分队,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令上下等级森严,层层指挥,不出疵漏。更规定将官脱离本阵时,除护卫随行外,本阵不得有任何变化。这样,即使遭遇突然袭击,也可迅速集中战斗力。若将官不幸身亡或无法指挥,迅速由下一级将官替补,这样,即使队伍打残,只要有一个将领存在,队伍便可凝聚,重新形成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