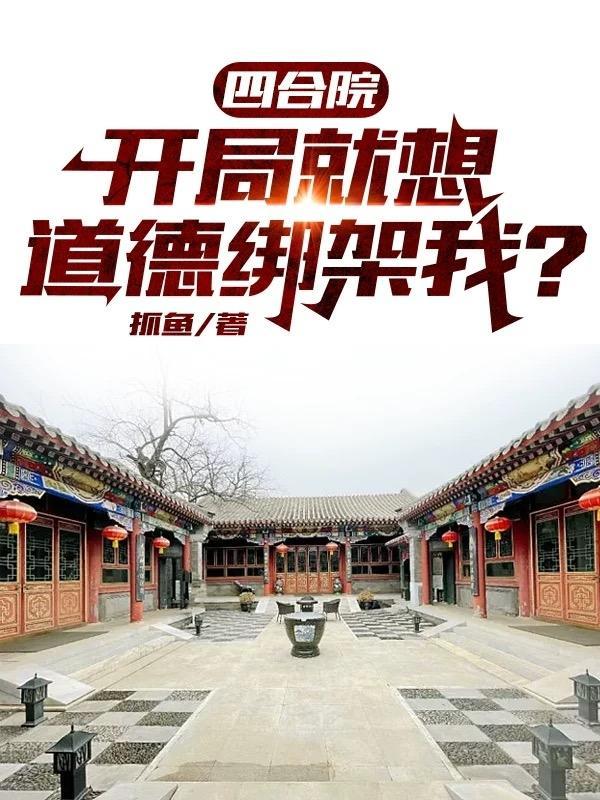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秘色瓷八棱净瓶 > 第一章 灵堂怪事(第1页)
第一章 灵堂怪事(第1页)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整个小窑村都沉浸在黑暗中。
杜铭川跪在灵堂正中的草垫子上,听见屋外的灵幡在风中簌簌作响。供桌上没有任何供品,只有一只香炉和一盏油灯。香炉里插着三根线香,袅袅青烟缭绕在空荡的屋子里。油灯的棉线灯芯燃起昏黄的光,忽明忽暗,仿佛极力要在生命燃尽之前给世界留下一点光明。可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除了勉强让人看见布幔上那个大大的“奠”
字外,它连墙上挂着的遗像轮廓都照不清晰。供桌后面没有灵柩,一块门板搭在两张长条凳上,门板上没有尸体,也没有被褥,却放着一只一尺多高的玉壶春瓶。
青色的釉面流淌着一层淡淡光晕,恍如夜幕中朦胧的天空,而瓶身上有一抹血色,如红云在天,显得极为突兀。这是整个灵堂里唯一的亮色,即使灯光昏弱,这只瓷瓶的色泽依然堪称美艳。
十三岁本应是个满是青葱和灿烂的年纪,而十三岁的杜铭川却失去了这一切。西方人说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因为耶稣的第十三个弟子背叛了他。据说有些国家的楼层里没有十三层,酒店的房间没有十三号。杜铭川曾觉得很好笑,原来西方人在传播科学的同时,比我们还要迷信。可现在他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十三年前,他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来到了这个江南小镇,他随之降生于世,到今年恰好十三岁。父亲是个烧瓷工,在这小窑村开了个瓷器作坊。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每年都要烧一批奇怪的瓷器,无论准备多少个瓷坯放进窑里烧,开窑后烧成的准是十三个。
除了这些,杜铭川仔细算算,他在这间灵堂里守灵,已经是第十三个晚上。这么多的十三,怎能不让他怀疑起这个数字的意义来。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这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背的《道德经》里的一句话。过去,他无法理解也不会去推敲这些深奥艰涩的文字,现在,他却不得不思考起生与死的意义来。
头上的白麻布缠得他脑袋有点沉,草垫子虽然很厚,跪着的时间久了,膝盖也会生疼生疼。油盏里的灯油已经不多,火苗变成了黄豆大小一粒,灯光渐渐黯淡下去。杜铭川保持着跪姿不变,轻微挪了挪身子,提起地下的油壶,往灯盏里添油。
火苗就像被放大镜罩住了一样,一下子变大了几倍,可以清楚地看见供桌上放着一块小小的碎瓷片,颜色和床板上那只玉壶春瓶一模一样,只是外面多了一层包浆,那是因年代久远而留下的岁月痕迹。瓷片的旁边还有一颗泛着乌光的子弹,如半截小拇指大小。
仇恨的火焰如添了油后的灯光一般燃烧起来,杜铭川捏住子弹,狠狠攥在手心里,指甲因为用力而陷进了肉里。但子弹的硬度岂是**能够破坏的,他深吸了几口气,将子弹放回到供桌上,轻轻摸了摸暗藏在腰间的匕。
一把匕,一个少年,有机会对付带枪的人吗?尽管希望渺茫,他依然决定一试。
屋外的风在盘旋,他知道那人一定会来,也许就在今晚——这第十三个守灵日。
里屋传来几声轻微的咳嗽,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格外真切。杜铭川的身躯抖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要站起来。父亲走后,母亲就病了,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杜铭川不得不用他那还稚嫩的肩膀扛起这个家的重担,一边办理父亲的后事,一边悉心照料母亲。每天晚上,他都要等母亲入睡了,才到灵堂里来守灵。他知道,只要一咳嗽,母亲就一定会醒来。
体弱多病的母亲躺在里屋的床上,而父亲的灵魂就在这灵堂里。该去照顾活着的母亲?还是留下来守着父亲的灵魂?杜铭川握着腰间的匕,犹豫着。他觉得今晚一定会生什么,那两个逼死父亲的人会不会现身呢?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留下了碎瓷片和子弹,不就是想要那只玉壶春瓶子吗!
&1t;aid="zsy"href="小说&1t;a>
安静了片刻,咳嗽声又骤然响起,一声接着一声连成了一串,比刚才剧烈得多。杜铭川的心揪了起来,比自己咳嗽还要难受。他连忙站起来,再也顾不得这边会生什么,急步穿过灵堂,往后屋走去。
里屋没有开灯,杜铭川在黑暗中顺着墙壁摸索,找到了那根电灯开关绳,轻轻一拉,二十五瓦的白炽灯泡亮起来,橘黄色的灯光将房间照亮。他看见母亲已经坐起来,靠在床头,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杜铭川在青瓷杯子里倒了点热水,端到母亲面前,轻声问道:“妈,您哪儿不舒服?”
母亲接过杯子喝了两口,示意他坐下,说:“我没事,就是做了噩梦醒了,睡不着。”
杜铭川稍稍放下心,把青瓷杯放到桌子上,回身给母亲拉了拉毯子:“晚上天凉,您别着凉了。”
母亲点点头,说:“我晓得的。你也别去守灵了,坐这儿陪我说说话吧。”
杜铭川有点犹豫,但还是在床沿坐了下来。母亲叹了口气,说:“铭川啊,已经十三天了,你也别再守下去了,石匠师父的墓碑都送来了,就拿些你爸的衣物葬了吧。”
“妈——”
杜铭川想说什么,又不想让母亲担心,喉头不禁有些哽咽。
“我知道你在等什么。”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我不阻止你,是因为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可你想想,你爸选择这么走了,还不是为了我们娘俩能好好活下去?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对得起你爸在天之灵?”
杜铭川的右手下意识地摸到了腰间,仿佛那把尖锐的匕还没有扎到敌人,却已经扎进了自己的心,一寸一寸。他颤抖着声音说:“我知道了,妈!”
母亲的脸色终于缓和下来,目光变得更加慈爱:“知道就好,那你去吧,守足了今夜,明天就下葬吧。如果今晚他们来了,你别冲动,要拿什么就任他们拿,记住他们的脸,将来总有机会。”
杜铭川回到灵堂的时候,油灯已经灭了。据说灵前的香火是不能断的,那是为了接引阴间来的使者,一旦断掉,死者很可能将成孤魂野鬼。好在油灯虽灭,香还在燃。但令杜铭川奇怪的是,他刚才添过灯油,按说不至于这么快就燃尽,而门窗都关得很好,不可能有风吹进来。
他不敢开电灯,老人们说那会惊吓到死者的灵魂。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杜铭川小心翼翼地走到供桌前,跪倒在草垫子上,摸着火柴盒,划亮了一根,看清灯盏里果然还有半盏灯油。
油灯重新亮起,杜铭川惊得跳了起来,急切地在四周寻找着。大门上插着门栓,窗户也从里面反锁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进来过,而供桌上的碎瓷片和子弹却不见了,再看床板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碧血玉壶春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