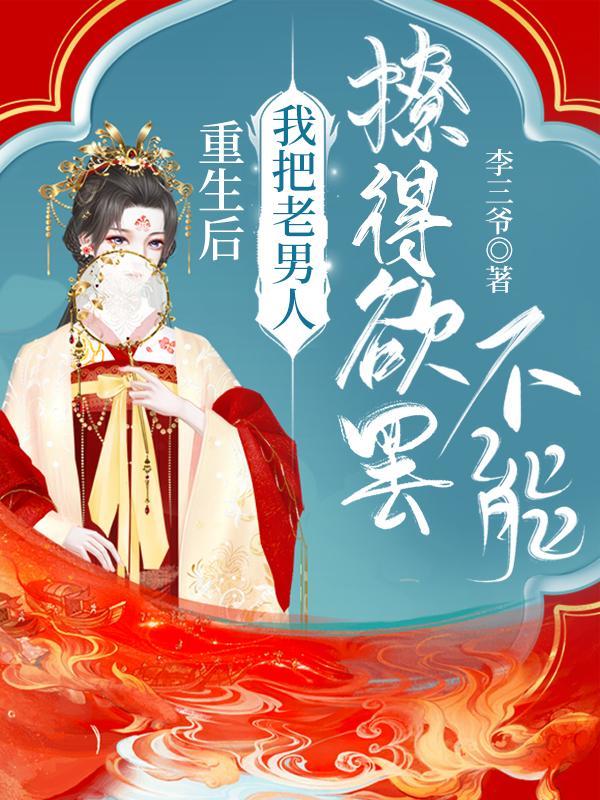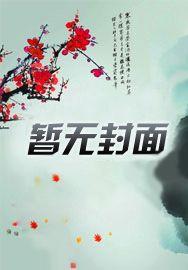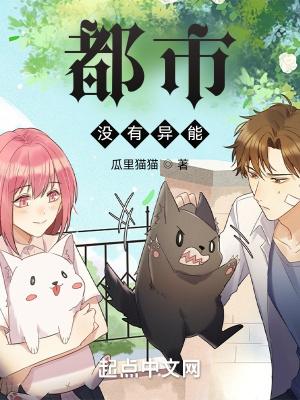69书吧>卧马沟的冬天杏花的结局 > 第二十一章02(第2页)
第二十一章02(第2页)
群情激奋一片昂扬,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任何地方都有人心背向,卧马沟也不例外。男人女人大人小人把灶棚围了个水泄不通。稀汤寡水的饭有啥吃头,可是不如看一场这样的争斗过瘾。
所有的人都围挤上来了,独独耀先一家三口坐在皂角树底下没有动,要说心情,耀先月儿也是和大家一样的,也是恨不得虎林兄弟狠狠地把那个可恶的黑脸贼挫一顿,把那个掌勺的刁蛮不讲理的丑女人也挫一顿。心里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却不敢凑到跟前去看热闹,怕过去了自己再惹上事情。新生活闪着眼睛想过去钻在人群里看热闹,让月儿一把拽住。小心的月儿连皂角树底下都不敢停了,她把馍盘菜碗端起来,小声对耀先说:“咱还是躲远点,回崖口上去吧。”
耀先第一次没有听月儿的劝告,他削瘦的脸上涌起一片少有的兴奋,把手向下压一压,示意月儿圪蹴下不要动。皂角树离灶棚远着哩,即是他们抡着砖头打起来也伤及不到这里,怕啥。咱啥时候能碰上这样让人解恨的事情。月儿理解耀先的心情,这么多年让这个黑脸贼整苦了,月儿也想看看黑脸贼让人整治的场面。月儿慌慌地再圪蹴下来,都不敢直端端地睁眼往灶棚底下瞅看,只是侧起耳朵细细地听。耀先不像月儿那么小心,他手里捏着一只空碗,扬起脖子使劲往灶棚底下看。一盆饭,一盘馍,一碗菜放在地上一家人都顾不上吃。
还是有拉架劝架的,李中原上去就把虎林的后腰搂抱住,不让他低着头往郭安屯的怀里撞,李丁民也撂下饭碗上去拉劝。
正在上房院吃饭的吴根才听见灶棚里吵嚷,手里捏着半个馍出来站在哨门底下,高声喝道:“吵啥吵。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还有劲吵架,是谁在那吵?有劲,后晌到地里使去。”
“队长,你赶紧过来吧,这里要打死人咧。”
有人喊叫起来,吴根才一听这话,就赶紧跑过来拨开人群,看见是虎林兄弟和安屯在争,就沉下脸说:“值当吗?多吃一口就胖了,少吃一口就瘦了。有劲攒在肚子里,也顶两碗饭。散开,都散开吃饭,吃完饭还上工哩。”
“不行。”
虎林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就要闹个结果出来,他看出来了,社员大都是站在他这一面,他是有理的,和去年偷玉茭穗子不一样。有理就要说到底。“根才,你是一个公道人,这个理就由你来说。”
虎林把吴根才拽到自己的那盆饭跟前让他看,这盆饭就是吵架的起因。“根才,你也是在食堂灶上吃饭的人,我的这盆饭能不能和你的那盆饭比。”
话说开了,脸撕破了,虎林也就不再顾忌什么了。人善被人欺,不当一回恶人,这辈子也别想吃饱饭。他直接拿吴根才和自己比起来。吴根才的脸红了,他看到的虎林盆里的饭,明显比女儿们端回的饭稀的多。“队长,你再来看看拴娃瓦盆里的饭是个啥。”
虎林疯了一样,拉拽着吴根才的胳膊,把他拉拽出人群,拉拽到皂角树底下的耀先月儿跟前。耀先领来的馍饭放在那里,还没有动一筷子,他们把馍饭放在那里不是为了让人参观展览,刚才看吵架是顾不上吃。虎林抢过耀先手上的竹筷子,在瓦盆里捞搅一下,稀稀的饭里捞挑不起几根面穗穗。“根才,你是队长,你说说这个理,人家成份不好,可人家也有一份口粮呀。吃不够十两,也得让人家吃够八两。你看看这够不够八两,成份不好,可也是人,一天三晌在地里比谁干的都不少。差不多就行了,差的太多就让人看不过眼,这差的就太多了。”
虎林让耀先月儿当了一回典型,这可把耀先月儿吓坏了,这样的典型他们那里敢当呀。也跟过来的郭安屯恼着黑脸正眼睁睁地瞪着他们呢,他肯定会想着是他们和虎林串通起来和他作对的。看热闹的人们也都跟过来,一下把耀先月儿围裹在正中间。
被人群围裹住的月儿慌乱的不敢往起抬头,她心里后悔死了,刚才要是端着饭盆回了崖口,就不会招惹来这样的是非麻烦。耀先也和月儿一样慌乱的语无伦次地说:“不碍事,不碍事,多一点少一点稠一点稀一点不碍事。”
吴根才盯着月儿的脸看了一阵,心里真有些难受。这种事情他倒是想到过,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彩兰真是太过分了,月儿每天后晌用手顶在肚子上干不动活,那就是饿的呀,一天喝三顿这样的稀汤饭,谁能顶的下来。“就是,这饭舀的太稀了。”
吴根才喃喃一声。“都是一样样的,只有你们几家是稠的。”
人群里一个声音响响亮亮地喊出来。吴根才宽大的脸上就有了愧疚的歉意。他的上房院离灶棚近,开了大锅饭后他差不多每天都是让女儿们把饭领回去在院子里吃,对灶上的事不完全了解,当然也是听到过一些意见的,但没有在意没有往心里去。吴根才回过头又看了几家饭盆里的饭,果然都是稀汤寡水的里面没有几根面穗儿。
虎林觉得火候到了,就煽动着说:“队长,你要是个公道人,就把灶棚里做饭的女人换了。”
“把掌勺的女人换了。”
“把掌勺的女人换了。”
虎林的话像是一块石头掉进水里,引起一片荡漾的涟漪,引起一片骚动的呼应。面对不公,只要有人敢挑头,老百姓就敢往上跟。
一直站在灶棚底下,手里掌握着长把大铜勺不松手的彩兰,听到这一片呼呼啦啦的喊声,气的把长把大铜勺往敞口锅里一撂,扭身进了官窑,坐在里面“挨炮子的挨刺刀的”
胡乱骂起来。
民众的呼声,谁都不可小视。倒不是说小小卧马沟的生产队长也和坐在殿堂之上的国家领导人一样,也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吴根才没有钻研过那么深奥的哲学道理。从善如流是人的天性,这一点他还是有的。吴根才毕竟是一个正派人,他不能因为一个亲家母,就把全村的人都得罪了,对彩兰他也是有看法的。
第二天灶棚里掌勺的女人就真的换了,换成李丁民的女人水仙。不是水仙自己出面要争这个差事,是大家伙推选她出来掌勺的。水仙和她的男人一样,在卧马沟有口碑,是一个和善勤勉的人。在水仙眼里亲家母改改和地主儿子的女人月儿都是平等一样的人,不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这样的人当然受大家拥护。
月儿这次还是没有进了灶房,水仙进去是想把月儿也叫进灶房的,月儿整齐干净是蒸馍做饭的好手。但是队长们没有搭话,和开始一样,还是郭安屯不同意,吴根才不好说话,因为是水仙提出来的,李丁民也不好说话,这事就又搁下了。
被大家从灶房里撵出来的彩兰站在坡道上狠着声骂了三天,这三天她都不上工了,只是不歇声地骂,见人骂人,见狗骂狗,见鸡骂鸡。人们以为这个女人也疯了,疯女人为啥都出在他们郭家?彩兰没有疯,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疯了呢,她只是撒撒野出出气而已。要疯她就不是郭安屯的女人了。
水仙在灶棚里掌上勺,再开饭的时候灶棚外的场子上就安静的多了,人们碗里的饭稠稀深浅都差不多,谁肚子里还能有气。老百姓不怕穷不怕苦不怕累,老百姓最怕的是不均。穷一起穷,苦一起苦,我饿着你饱着就不行,就没有道理,你饱是多吃了我的份儿才饱了的,我能服气?水仙一掌勺这些怨气就都没有了,场子上没有了吵闹只有一片呼呼噜噜的吃饭声。
大锅饭一开,学校里的皇甫老师也到大灶上来吃饭,原来他吃的是派饭,一个学生管一天,饭轮流转。派饭当然要比大锅饭好,无论谁家管老师的饭都像正月里待客一样尽量捡好的做。卧马沟的世代农民巴望着皇甫老师能把他们的子弟调教出来,不仅调教的能识书达理,最好还能调教的出去干了事。在外面给公家干事的人就是比种庄稼的人强。沟里的庄稼人,一年割一次麦分一次红,干事的人月月有个麦儿黄,一个月领下的工资比种庄稼的老百姓一年分的红还多。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卧马沟人的这种心愿就体现在管皇甫老师的饭上,前两年谁家管饭都是三盘五盏地放在提盒里往皇甫老师的窑里送。在皇甫老师身上寄托着卧马沟人的多少梦想和希望。吃了卧马沟学生家长送来的盘盘盏盏的美味可口的好饭,皇甫老师感到一阵阵的惶恐,一个小学老师那里承载的起这么厚重的希望,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拿出自己全部的看家本领,都惟恐不够。困难时期来了,生产队开起了大锅灶,学生家里都开不起伙,自然也管不了老师的饭。皇甫老师就端上碗也到大灶上来吃大锅饭,这大锅饭倒让他吃的心安理得,自己肚子里的那点本事也就配吃这样的饭。
皇甫老师端着饭菜过来圪蹴在耀先一家跟前。灶棚里换了人,水仙掌勺后耀先一家再领回来的饭就不再是只漂着一层油花子的稀汤寡水,他们黑瓦盆里的饭也和大家一样稠稠糊糊的有不少面,能和大家一样受到公平的对待这让他们感到万分的欣喜。心里高兴不高兴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现在耀先月儿脸上就洋溢着一种自然真诚的笑。他们用这种自然真诚的笑脸迎住主动端碗过来的皇甫老师,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一般人都不愿意往他们跟前凑,皇甫老师能端着碗过来,真让他们感动。皇甫老师过来是想跟耀先说说新生的事情,这次全公社统考,新生又考了个全年级第一,这是一个好苗子,放在自己手上他怕屈了材。“耀先,你们家新生真是伶俐呀。”
皇甫老师过来先夸新生一句。
耀先赶紧说:“这全是皇甫老师教的好,能遇上你这样的好老师,是新生一辈子的福气。”
耀先和月儿知道新生又在全公社考了个第一,但他们没有沾沾自喜,他们把这份成绩,这份荣誉归在皇甫老师名下,他们向皇甫老师表达的是最真诚的谢意。“哪里呀,是新生自己有这份天赋,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那点水。”
难得呀,人贵有自知之明,皇甫老师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低声再对耀先说:“新生这孩子将来肯定能有大出息,我的这两把刷子真的不行,我有一个想法,为了不影响孩子将来的前途,你们还是想办法把孩子转到三合镇去吧,三合镇学校里有个好老师,是省上下放来的一个右派,断了一条腿,但教书没的说,现在连县城里的干部都把孩子往三合镇送。”
耀先月儿怎么能没想到儿子的将来呢,儿子的将来也就是他们的将来呀。耀先月儿日日夜夜想的都是这些,十多年来他们过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呀。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不幸的生活,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能使这种苦难和屈辱的生活得到根本彻底的改变,希望儿子最终能使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希望儿子能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希望儿子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在儿子身上他们寄托着太多太多的期望。但是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他们不可能把儿子送到三合镇那样的好学校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条件不允许,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条件都不允许。他们是被管制的对象,连卧马沟都不许出去,怎么又能把儿子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对三合镇耀先是很熟悉的,小时候他就是在三合镇的三官庙里上的学。可是现在不能和过去比。耀先苦苦地笑笑,说:“缓上两年,现在是困难时期,等困难过去再说这事。”
皇甫老师端起碗吸溜一口饭很认真地说:“这可是件正经事,孩子的前途是最要紧的,缓两年也行,三合镇有中学,中学一定要让新生去那里上。”
月儿看着皇甫老师感激地笑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诵一句:但愿新生能到三合镇去上中学,但愿新生将来能有大出息。
水仙掌上大灶上的勺把子时间不长,就替吴根才愁起来,这怎么能长久呢?全村这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张着一张嘴到点就来吃,到点就来吃,真的就是吃上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了。可现在还没有到了共产主义,现在是困难时期,库房里的粮食不是丰满的装不下溢的往外流,库里就那么一点点粮食吃完了吃啥呀?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这是整个卧马沟全村人的大问题。水仙和卧马沟所有的女人一样,没有文化,对大道理知道的不多,但是对共产主义还是略略知道一些,这些年来只要公社县里下来干部,无论是多大的人物,都会对老百姓天花乱坠地讲说一通共产主义,就连山上的瞎眼老婆婆都知道共产主义好: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家家柜满囤溢,穿的吃的不愁,人人布袋里都有花不完的钱票票。实际呢?实际上是个啥?干部们说了这么多年,却让老百姓过上了困难日子,连饭都吃不饱了。这往后干部们说的话还能再信吗?美好的共产主义还敢再想吗?
水仙真的替吴根才愁,替吴根才愁实际上也是替自己愁,替全卧马沟人愁。水仙每天都要进库里去领兑粮食,库里就那么一点粮食,领一点就少一点,眼见着就没了。库里的粮食没了,那敞开口的大锅饭还有么?锅里没饭了,全村人拿着碗过来吃啥呀?水仙不敢把这话说给吴根才,就先说给自己的男人李丁民。
一向稳稳重重的李丁民心里也咯咯漾漾地沉不住气了,可他又有啥办法,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赶上困难时期了,上面统一安排让搞大锅灶,你不搞能行吗。“唉!”
李丁民把他那细长的眼睛眯缝起来,深长地哀叹一声,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作用就像是河滩里的一粒沙子,太小太小太微不足道了。
谁说吴根才不愁。吴根才愁的头顶上都有了白丝,原来他可是有一头乌顶顶黑的黑头呀。保管员李中原五次三番地在他耳根子底下说:库里的粮食不多了,库里的粮食不多了。多不多还用你说,吴根才当了这么多年队长,心里还能没个底,就和自己家过日子一样,他知道队里的底子有多厚。穷家难当,他比谁都愁的厉害。卧马沟三十二户,原来就有三十二个当家操心的人。穷日子富日子自己当家自己过,各操各的心,自己的娃子自己哄,自己的老婆自己养。现在可好,原来的三十二户变成集体一户,原来三十二个当家操心人,现在都成了甩手大闲人。不分口粮不开伙,谁还能操上心。他吴根才就成了全卧马沟唯一的当家人,他一个人承担起原来三十二个人才能承担起的责任。山一样重的责任都快把他压爬下了,他那里能承担的起。去年的困难比今年大,把口粮分下去,大家各操各的心,都熬挺过来了。今年把口粮集中起来吃大锅饭,这日子就难熬。把口粮分下去,就是把大困难分成小困难。小困难就要比大困难好对付。去年分的口粮那么少,大家各想各的法,挖野菜,捋树皮,摘山果,打荆条籽都想着法儿过来了。可是今年开了大锅灶,谁还再想着去挖野菜捋树皮摘山果打荆条籽,到时候都端盆拿碗有理气长地到灶上来领饭,好像灶上的饭永远也吃不完,好像灶上的饭真就是官饭,不吃白不吃,吃官饭还用操心。错了,乡亲们,豁豁吃鼻涕各人吃各人。是大锅饭,但不是官饭,大锅饭里熬煮着的还是自己的那点口粮,吃完了就把嘴吊起来了。“这是那个缺德没尻眼的家伙想出来的大锅饭,这不是成心糟蹋老百姓吗。”
愁的展不开眉的吴根才在心里狠狠地骂起来。
吃大锅饭真的不是个好办法,一吃大锅饭人们就连思想都懒惰了麻木了,就都啥法儿也不想了,就都懒懒地靠在这口大锅上张着嘴等着开饭。这是困难时期呀,都不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日子咋过?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都他妈的甩手不当家了,真的都不知道现在还是在困难时期里。吴根才还想把卧马沟这些甩开手不再操心的人再狠狠地骂上一通,还没有开口,保管李中原又来了。“队长,你得赶快想法呀,咱库里的那点粮食眼看着就要完了,大锅灶塌伙了这一村人可咋办呀?”
“咋办?吃松喝凉水去,我还管得了那么多,都不操心,都当了甩手吃闲饭的人。大锅灶塌了都把嘴吊起来,我也不管毬这事咧。”
吴根才还是着火骂出来。
着急上火解决不了问题,政治队长郭安屯又想出办法来了,郭安屯真的成精了。
郭安屯是在公社开了两天会把办法带回来了。这办法不是他自己想出来,他没有这个能耐。这办法还和大锅灶一样,是外面传进来的宝贵经验。现在整个国家都在困难时期,吃大锅饭也不是卧马沟一个村子,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全国都在吃这种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就是说那里都和卧马沟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相似的问题。许多人的处境都和吴根才差不多,吴根才老实厚道面对这样艰难的处境束手无策想不出应对的办法,他没有孙猴子的本领,拔一根腿上的毫毛就变化出无数的粮食。他不能,有人能。中国地大物博能人辈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熬淀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