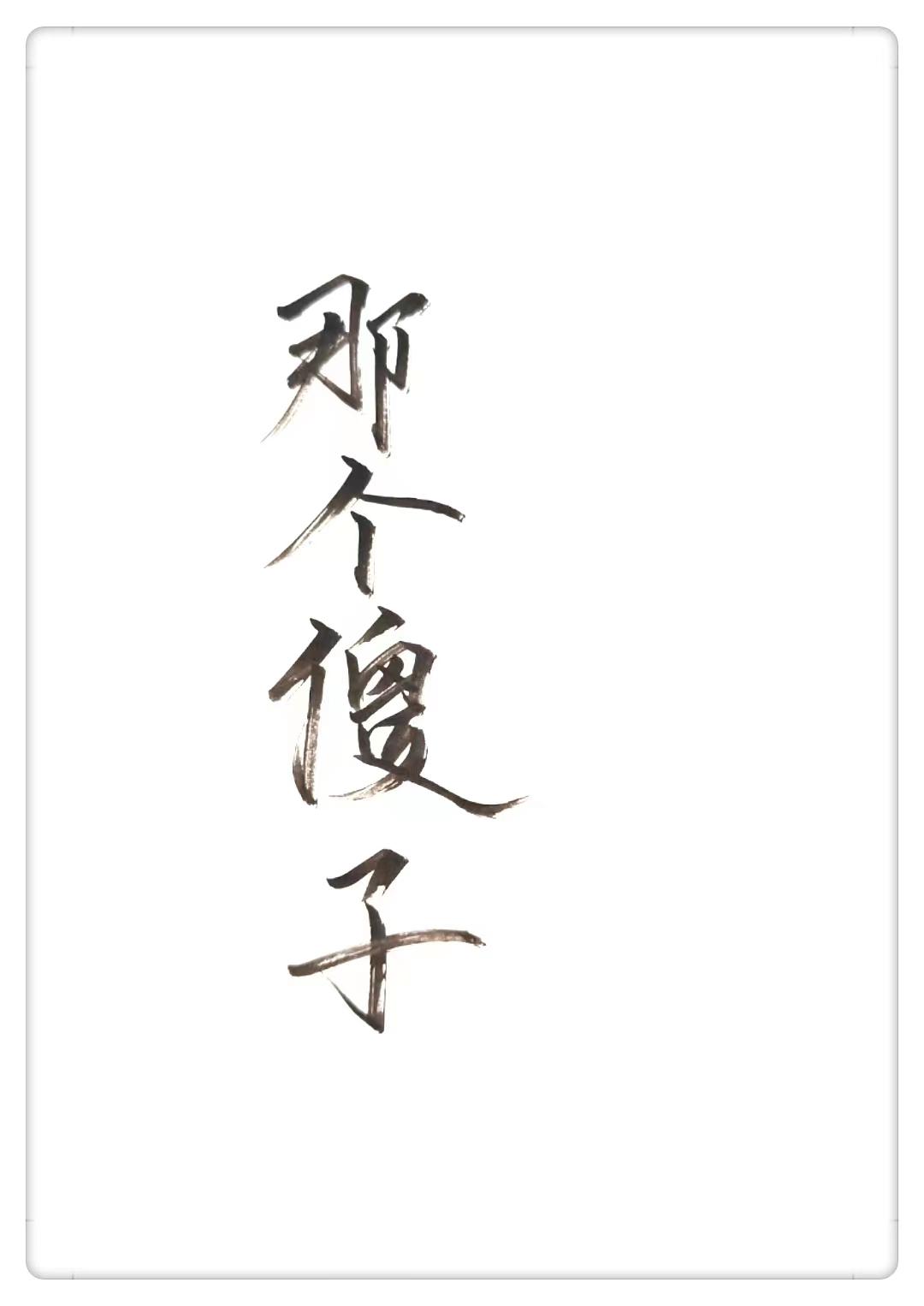69书吧>状元游街的诗句 > 第15页(第1页)
第15页(第1页)
他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勉强抑止怒意,沙哑地道:“你不是我师父。”
他以为李去非会反驳,像以往无数次那样,把全副心思转到让他唤她一声“师父”
上,然后用不到一刻钟,她便会完全忘了现在说过的混帐话……是的,他们过去一直是如此相处,将来……永远都会维持原状!
李去非手上把玩折扇的动作一顿,回过头看着赵梓樾,莞尔一笑。
“你仍然坚持做我的书僮?也罢,就算你是我的书僮,家仆更不能违逆主人。”
见赵梓樾又要张口,她抢先道:“你难道又想否认你是我的书僮?你若不是我的弟子,不是我的书僮,那……你我算何种关系?”
赵梓樾被她问得张口结舌,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心底隐约觉得李去非问得对。是啊,他不肯做李去非的弟子,虽然自称书僮,也从未真心要做她的仆人,那么,他和李去非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十三岁遇到李去非,相依为命五年,她教他养他,亦师亦母亦姐亦友,他心存感激,暗下决心要照顾保护陪伴她,从未思及其它。他见识过人间丑陋,蔑视所谓世俗道德,李去非的身份更是惊世骇俗,他一向以为,世上没什么能分开他们……他却忘了,他们到底非亲非故男女有别,不是师徒不是主仆,当她有所置疑,他又能依靠什么样的身份继续赖在她身边?
赵梓樾生性本来激烈,易怒易乐大喜大悲,却因为幼时的遭遇,跟随李去非后拼命压抑自己,装作冷面冷心。此刻思绪繁杂纷乱,失去了控制力,翻江倒海的情感淹得他透不过气……李去非又瞥了他一眼,轻轻拨开他抓住她的手,赵梓樾惶恐地、近乎哀求地看着她。
李去非背转身,举步走上台阶。
“你既不是我什么人,也没必要再跟着我。”
“罢了。”
“你走吧。”
又是“罢了”
!
胸中被揪扯的疼痛更甚,让赵梓樾想嘶吼,想责问李去非,“罢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他又怕,怕他得回的是避之惟恐不及的答案。
赵梓樾立在雪地中,眼望李去非拾阶而上的背影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的脸色愈惨白,突然一顿足,青色身影飞跃上对面一幢民居屋顶,兔起鹘落间已不见人影。
“什、什么人?!”
扫雪的差役瞥眼间看到,“刷”
一声拔出腰间钢刀,快步赶到赵梓樾跳上屋顶的房屋前张望。人影不知所踪,脚下却感觉有些凹凸不平,差役低头再看,倒抽一口冷气——青石板上竟被踏出一对深深脚印!
偏他受的惊吓还没完,一口气刚吸进肚里,府衙方向传来的击鼓声又让他情不自禁再出“咝”
一声。
“咚!咚!咚!”
“一声告民,两声告官,三声冤重,青天开眼”
。
卯时一刻,鸣冤鼓沉闷的鼓声回荡在嘉靖府衙前,天空中,厚重的云层缓慢合拢,不见阳光。
第十章丞相字
三声鼓响过,公堂敞开大门,青天白日照壁闪闪亮,穿着整齐公服的皂隶排开两列,水火棍把硬梆梆的地面敲得山响。
冯知府一摇三摆地从后衙出来,人未到声先到:“将击鼓人带上来。”
李去非被一把推进公堂。
真是粗鲁。她嗔怪地斜了一眼身后魁梧如熊罴的衙役,及时上前两步,避开他再次伸出的熊掌,抬头望向堂上。
公案后坐着官服的冯知府,身后一左一右立了两人,左边的青年仆从打扮,低着头看不清脸,右边是一名中年儒生,眉眼间透着精明。李去非的目光分别在两人身上溜了一圈,猜到右边那人是冯知府的师爷。至于左边的青衣人……她先是蹙起眉,旋即绽出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心道,天幸这人在此,赵梓樾犯的错还能弥补。
衙役上报道:“大人,击鼓人带到。”
冯知府点头,也不看李去非,举手落下,惊堂木响亮地击在公案上,两列皂隶立刻配合地敲打水火棍,齐声沉喝:“威——武——”
这一整套有个名目叫“杀威”
。端王朝律例,刑讼是不能已而为之,为免小民因为鸡皮蒜皮的事也去告官,凡原告必先杀其威,希望他能知难而退。
皂隶的沉喝和水火棍的敲击停止后,冯知府觉得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不禁咳嗽了一声,忍住揉耳朵的欲望,第一次正眼看向堂下的原告,然后怔了怔。
通常“杀威”
过后,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民会吓得双股战栗当场下跪,就算乡绅巨贾也不免脸色青,面对着公堂代表的赫赫天威国法百里百里,再心志坚定的人都要肃然起敬。
但显然,今天遇到了例外。
堂下立着一名书生,端王朝弘扬文治,秀才与七品官员同级,公堂上免跪。
那书生头戴秀才巾,长却随意地挽在脑后,想是怕冷的厉害,身上穿了不知几层棉袄,鼓鼓囊囊像个棉团,愈衬着一张脸小得出奇,五官清秀娟好如女子。但你说他怕冷吧,手上居然还执着一柄折扇,还时不时把折扇挥开,故作潇洒地扇一扇。
更令冯知府微怒的是,那书生竟毫无敬意地直视他这位牧守一方的父母官,一张肖似女人的脸上笑容可掬。
那书生微笑着拱了拱手。
“丞相大人门下,闲人李去非拜见冯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