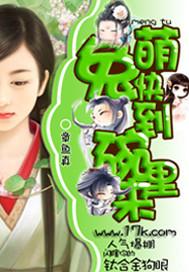69书吧>老村长淡雅酒42度480ml单瓶多少钱 > 第15章 赵启章家的麦秸垛着火了(第3页)
第15章 赵启章家的麦秸垛着火了(第3页)
赵启章这边嚷嚷一阵子也只好回家去的。
几天后,两家真的打起了官司,但原告不是周顺昌,而是赵启章,主要也不是因为这次打架,而是因为接下来生的一件事情。
就在这次打架三天之后,赵东城夜里起来小解,无意中向北边的天空望了一下,忽然现天空一片红光。
他凭经验知道可能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就赶紧跑到屋后去看个究竟,只见北边场地方向不知谁家的麦秸垛着了起来,火焰打着滚向上直蹿。
这时因为嫌热而在场地附近睡觉的人,已经有人在叫喊,村里马上就嚷乱了起来。
赵东城一边向村里喊着:“救火呀,赶紧起来到北地麦场救火啊。”
一边转回院里,拎起一只水桶就向着火的场地跑去。
他跑到地方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救火了。
场地旁边没有水井,也没有水的水沟。
有人用铁锹向着火的麦秸垛上甩土,但灭火的效果不大。
赵东城跑回村里拎水,但是火势这么大,半天拎来一桶水根本就不顶用。
这时有人喊道:“这是赵启章家的麦秸垛,他家的人呢?咋不见他家的人来?”
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排成队开始从村里往场地传水。
过了好大一会儿,赵东城才看到赵启章急匆匆地跑来,而这时候麦秸垛已经整个着了起来,火苗向上窜起足有数丈之高。
人们被热浪烤得几乎不能近前,整个场地亮如白昼。
赵启章来到后并没有动手去救火,而是冷着脸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他家的其他人也先后赶到了,都在忙着救火。
赵启章老婆看赵启章站着不动,就冲他喊道:“你咋不赶紧拎水,烧完了牲口吃啥?”
赵启章楞了一会儿,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不用救了,救了也没用,牲口不会再吃这麦秸了。”
救火的村民看他这样,也都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动作,后来有人干脆学他站在一旁,只是看着,好像是在欣赏什么迷人的风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在不停地来回跑动着。
大火一直烧到天明,麦秸垛成了一大堆黑灰,黑灰的内部还在不断地向外冒着滚滚的浓烟。
天一亮,赵启章就赶到镇里去报案。
他跟派出所的人说,他怀疑是周顺昌放的火,理由就是几天之前他们两家打架了,而且周顺昌以前对他一直有意见。
派出所的人来村里调查,周顺昌当然不会承认火是他放的,说赵启章这是栽赃陷害。
周顺昌又跑到镇里去找人,说赵启章诬告他。
也不知道他找了谁,反正派出所没有再找他的麻烦。
赵启章见派出所并没有把周顺昌怎么样,就到镇政府里找人活动,还跑到县里寻求支持。
但镇里要他拿出证据来,说没有证据,不要信口乱讲。
县里也只是要求镇里要妥善处理,其他也没多说什么。
赵启章这才隐隐感觉到自己可能大势已去,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要是以前生了这样的事儿,他到镇里一句话就能把周顺昌抓起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他又相信起自己原来的感觉来了,
很多迹象都表明他当初并不是敏感过度了,而是事实确实如此。
虽然镇里按惯例答应补助他4oo块钱,但这并不能让他心情轻松起来,
毕竟,在这件事情上,脸面比钱重要得多。
村里渐渐开始有人议论了,说赵启章当着书记,跟人家一个普通老百姓打官司,却没有打赢,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赵启章只得装糊涂,对此听而不闻,
他甚至在村人面前绝口不再提麦秸垛被烧的事儿了。
虽然赵东城对赵启章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他并没有对赵启章家的麦秸垛被烧感到幸灾乐祸。
他觉得,一个心地不纯正的人总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惩罚或报复一个人并没有必要用烧麦秸垛这种方式。
一方面一件事情的生,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另一方面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了,完全可以采取正当方式予以出击或者回击。
赵东城现,赵启章真的变了,他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无论面对任何事情,都信心十足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郁,好像他时时刻刻都在心事重重。
赵东城不由得感叹,真是世事弄人,精明通达如赵启章,竟然也会遇到排解不开之事,也会有失去奋争的勇气,无奈躺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