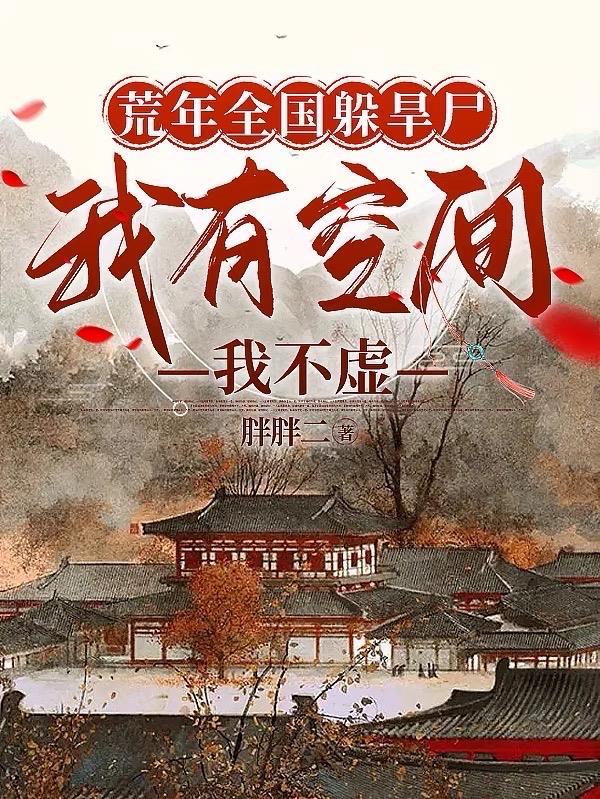69书吧>毒妃重生病娇王爷 > 第14章 夫妻之间无需道歉(第1页)
第14章 夫妻之间无需道歉(第1页)
清风一把推开殿门,将崔翌惊了一跳。
“翌公子,陈先生,殿下醒了。”
“表哥醒了?”
崔翌喜出望外,拔腿就跑。
几人紧随其后。
寝殿门窗四开,药味都散了不少。
崔翌勃然大怒,“你们做什么吃的?明知表哥见不得风。”
侍卫丫鬟连忙跪地请罪,头都不敢抬。
层层叠叠的帷帐后,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我让开的。”
大抵是身体太弱,不过一句话的功夫,就累地他呼吸急促,强压的咳嗽声丝丝屡屡地溢出来,听地崔翌眼睛一酸。
“表哥别动气,我不说就是了。”
萧衍掩着锦帕,不动声色地咽下嘴里的血腥气,“外面闹哄哄地,怎么回事?”
陈先生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崔翌恨地牙痒痒,“大理寺,刑部,锦衣卫,还有那废物礼部,平素耀武扬威,如今倒缩头乌龟一般,竟指望着秦王府去收拾残局。”
萧衍伏在榻上,耐心地等这阵眩晕过去,“有人不让处置罢了。”
“谁?”
崔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宫。
陈先生作恍然大悟状,“能让锦衣卫都作壁上观,只怕是陛下……还想再逼殿下一把啊。”
陛下终究是不死心,还想再逼殿下重新入朝。
崔翌咬牙切齿,“那表哥是非管不可了?”
萧衍默了一瞬,十分冷漠地开口,“不吃不喝,三五日还行,一两月恐怕没人熬得住。”
反正他有的时间去熬,渤海之后,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科举舞弊可是要动摇国本,殿下当真不管?”
陈先生试探道,“殿下浴血沙场,刀山火海地闯过去,才有了国朝如今的繁盛,一腔热血付之东流,您……当真忍心?”
他一面说,一面给崔翌使眼色。
“是啊,表哥,太子和齐王再怎么收买人心,也不及您分毫。”
萧衍静静地听着,等他们说完才开口,“太子仁德,你们若能去投奔他,我乐见其成。”
崔翌立刻急了,恨不得赌咒发誓以证清白,“您不管就不管,又何必说这气话来堵我的嘴。”
“若无事,早些回清河罢,免得高堂挂念。”
这些年,跟着他的人走地走,散地散,唯有崔翌和陈不平始终不死心,软硬兼施都没用,他也实在没法子了,只好由着两人。
崔翌俊朗的脸上划过一丝受伤。
他不怪表哥,只恨自己,要是他再有用些,再聪明些,表哥不会重伤,更不会这般郁郁寡欢。
“翌儿不走,打死也不走。”
崔翌一把掀开帷帐,赌气道。
萧衍叹口气,“那就安生呆在王府,低调行事。”
搁在被外的小臂疤痕累累,骨节修长的手几近透明,隐隐能看见肌肤下流动的血脉,崔翌半跪在榻前,为他仔细掖好锦被,“翌儿都听表哥的。”
只要别再赶他走。
陈不平见崔翌已经叛变,只得闭眼长叹,看来这大好机会又要溜走了,说句良心话,陛下的耐心着实不多,却堪堪有一大半花在了秦王殿下身上。
殿外忽地传来清风的声音。
“殿下,那些考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