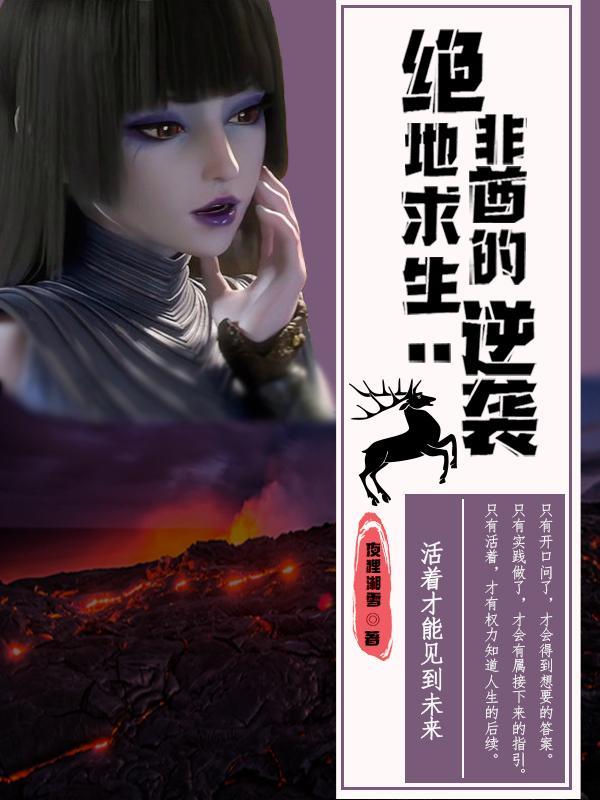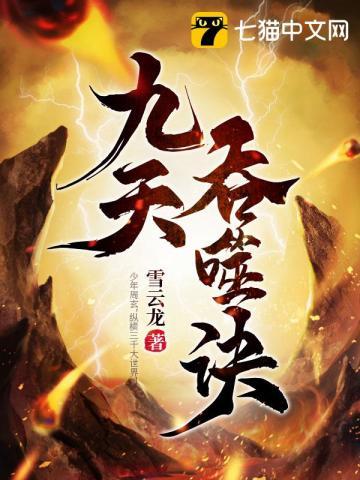69书吧>西出阳关有故人TXT 百度 > 第43节(第1页)
第43节(第1页)
“楼上可有住房?我们一行八人,麻烦准备四间房。若是方便,再准备些吃食,我们倒不算饿,主要是外头还有二位,已是饿得皮包骨了。”
许锦之语气客气,从钱袋子里拿出钱来,欲付给他们。
那两位难民,也随之进了屋子。
伙计们面面相觑,最后是一位最年长的起了身,叹了声气道:“贵人,我看您面善,和前头那位秦宣抚使一样,是个好人。但河阳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你们还是走吧。”
“此话怎讲?”
许锦之扬眉。
伙计还没来得及回话,那俩难民倒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口了。
“于县令,就是咱们河阳的土皇帝,当地所有的官员、富商家族都唯他马首是瞻。灾情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朝廷是派了人来赈灾的,也派了人过来修大坝。但是,几场大雨过后,朝廷派来的人,莫名其妙死在了河里。大坝也决堤了,咱们老百姓哪里经得住这么耗啊。”
“大家都知道于县令有问题,可又有谁敢问呢?有关系的、帮着糊弄的,能喝到几口粥,那些刺儿头,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饿死。时间久了,大家也就都服了。”
伙计们面露恐惧,好似在说:你们怎么把什么都给说出来了。
许锦之倒是很欣赏这两个仅剩不多的“刺儿头”
,他再次询问伙计,店里还有没有吃的。
伙计叹了口气,从后厨端出几块土馍,又拿出半壶浊酒,放到案上,“就这么多了,贵人们省着些吃吧。”
俩难民看见土馍,眼睛发光,直接冲上去,抢了塞进自己嘴里,哪怕噎得直翻白眼,也不肯停下。
“慢些,慢些吃。”
甄祝看不下去,从行囊中,将自己吃剩的肉干取出,拿给他们。
看见肉干,伙计们眼睛也亮了,不停咽口水。
许锦之见况,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吩咐随风:“将我们带过来的干粮,都给大家分了吧。”
“是。”
随风应道。
待俩难民和伙计们都吃饱喝足了,许锦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进行深一步的问话。
俩难民都是底层百姓,好不容易见着一个肯听他们说话的高官,便将苦水往外倾倒,根本停不下来。
“咱们河阳女多男少,当年打仗,家里的青壮年都被抽调上战场去啦,到后来,家里的老父亲也得上,家家户户只剩下老弱妇孺,田里的庄稼根本没人管,就大片大片烂在那里。可是,除了家家户户的一亩三分田,别的田都是朝廷租给我们的呀,交不上税,就只能欠着。”
“吃不上饭,又交不上税,人人饿得皮包骨头,只能去山上挖草根、啃树皮。。。。。。后来,山都被我们吃秃了,便只能吃人了。一开始是吃死人,后来就有人当街杀人拖回去煮了。体弱者,宁可饿死,也紧闭门窗,不敢出门,怕被人一棍子敲晕,拖去吃了。”
“后来,来了个于县令,一开始,他假模假样地想了很多办法,又是给单身女子找婆家了,又是给生得多的妇人奖赏米粮了。他鼓励寡妇再嫁,甚至还教妇人们如何打扮,吸引附近乡里的男子前来入赘。那时候,我们也过了几天稍稍平稳的日子,但天下当官的都一个狗样,很快,于县令就变了。大家伙儿都说,他这是把咱们当猪,养肥了再杀呢。”
大家听得沉默。
店内伙计们,算是百姓中比较有见识的人,知道的,也就多一些。
年长的伙计,告诉许锦之:“我们春满楼,原先也是河阳县数得上名号的酒楼,自打洪灾来了,我们掌柜的跑去外地躲难了,留下我们守在这里。洪灾过后,就是灾荒,就是疫情,百姓们为了活下去,看见吃的便抢。我们也是为了活命,才把匾额摘了,整日苟在其中。”
“再说那个于县令,他之前逼咱们下河捕捞鲤鱼,这可是要打六十板子的大罪啊,我们掌柜的不肯。他又让我们把酒楼重新装饰一遍,买一些好看的小姑娘放在店里做招待,再将吃的卖贵,我们掌柜的还是不肯。最后,我们酒楼老有人闹事,后来就开不下去了。”
“说起来,我们掌柜的虽然胆小怕事,但到底心不坏,他临走前,给了我们好些吃食和家当,不然,我们也撑不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