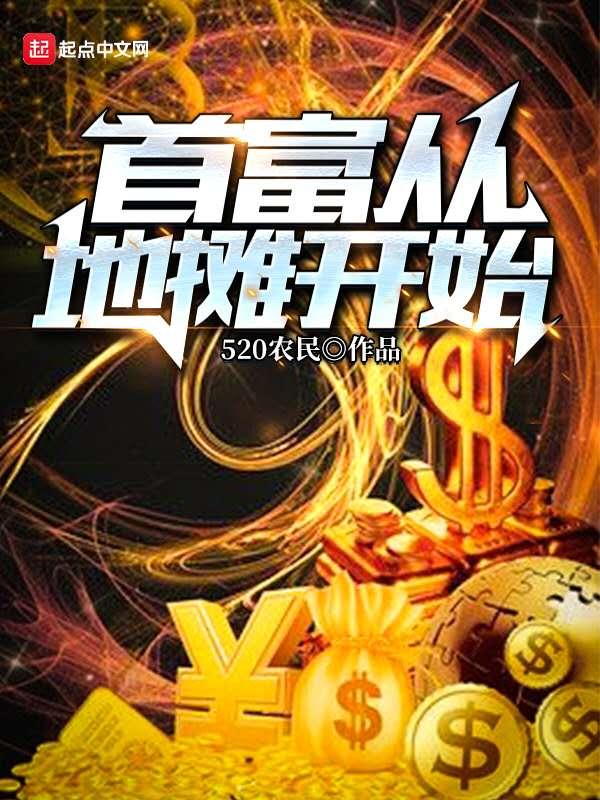69书吧>你是我的命运国语中字免费观看 > 第110页(第1页)
第110页(第1页)
这种死而复生的事在沈安之的灵魂体上共生了两次。诸位很清楚,百年前,在馥家出事后,由于沈家主母以死相逼,沈安之被迫成婚,娶了井世昌的大女儿井雨桐,诞下沈家子嗣沈一贞后,沈安之便丢下沈家和那对母子上了战场,而后死在战场上。而当时他的确是应该死了,而身体却奇迹般被转移至扶国,这一切与沈家消失于京海有关。
据传闻沈安之是沈家独子,沈家主母本就身体不好,得知沈安之离世便即刻吐血身亡,沈决也因此伤心欲绝一病不起,丰厚的家业便顺理成章全部留给了井世昌,这些均不假,但在表象背后往往会隐藏一个个不被人所皆知的真相。
沈安之醒来时,躺在扶国乡间的一栋僻静的小房子里,井雨桐穿着扶国的服装坐在他的身边,说着流利的扶国话,沈安之这才了然,井雨桐本就不是国人,她也第一次毫无掩饰的暴露自己的身份,显然一切都已经安置好了,无需再掩饰什么了。井雨桐眼中透出早已盘算好的莫测之态,拢着袖子,为他擦了擦额上的汗,掖了被角后,故作姿态提着欣然的表情道,“安之,你终于醒了。”
井雨桐这一套歉然又温和的动作,亦是久别,任谁人看着都觉二人无比恩爱,可是沈安之眼中透出着明显的失望之色,他眼风里分神望了望,大概有些明白了,终抖动着嘴唇问道,“现在是几月几号?”
他与井雨桐结婚无非是给沈家个交代,并留下个后人,忍得艰辛,而他遗弃家人,只是想在死后能够再用灵魂去深深地看馥汀兰一眼,继而他宁愿在战场上故意求死,可是寻着馥汀兰,真是件艰辛的事,甚至于连死都没有了资格。此番他又躺在了别人的怀里,被抱着甚是吃力的一点点活过来,每每入夜,被那一双从未有过情感的手柔柔的抚摸着,心中都有一股清冷,徐徐荡漾的想要呕吐。
“安之,我是不会让你死的,更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我知道你从未爱过我,是我非要嫁与你,但是我们是拜过堂的合法夫妻,如今我们将国内的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在这别处享人间烟火,你不觉得这是天意吗?”
井雨桐那模样带着几分腼腆羞涩,实则眼神深处埋着无法形容的心机,野心勃勃,委实强悍。
“我父母可还好?”
沈安之掐指算了算,距离他在战场上最后有知觉已过去足足半年,且不说这井雨桐编纂了一通冒着性命之忧救他与水火之中的故事,单是凭她的能力将他神不知鬼不觉运到扶国救活,就是一个让人打不清东南西北的迷局。
“你父母……”
说到这里,井雨桐故作姿态矜着泪,缓缓道,“安之,你父母因为你受伤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都不在了,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好好安置了二老,并将骨灰安置在咱们现在住所的祠堂里,你身体好些就可以过去看看他们二老。”
井雨桐哀切又希翼地将沈安之望着,很快擦掉了泪,换上一副娇羞模样,“我们都能完好的活着是十分不易的,你要为了咱们的贞儿考虑,他不能没有爹爹。”
见沈安之一副哀切的神情,她便轻轻将手抓住了沈安之的手,轻轻抚着,“等你这几日好些,我让贞儿来好好跟你说说话。”
沈安之瞧着她一副怀春模样,默默无语的躺在床上,像死人一般,神情十分颓废。不觉心中悲叹一声,沈安之啊沈安之,你堂堂正正七尺男儿,过不了祖训的关,现在亦过不了这情苦的关,活着亦是死了,罢了。
眼看井雨桐就要压在沈安之的身上,许是急火攻心,他捂着胸口吐了一口血,吓得井雨桐赶忙喊了大夫。
几名扶国的医生慌忙窜过来,为沈安之的手臂注射着针剂。有人用金属的器械听着他的胸口,判定没有大碍,方才离开。
被这样一折腾,沈安之有些困乏,借势闭上了眼,朦朦胧胧间眼前全是馥汀兰,问他:“说好的永生永世呢?”
病一场不过就是受些苦,可是伤一场,便是永生无缘。像他这等被迫逆天改命的人,不知在生死薄子上还会不会有名讳,总之,他因此彻底变了一个人。
话说回来,陈思源这副身体每周都要注射一次针剂,有一个就连陈思源也不清楚的人,在控制着这个永生世界的门,会着人定期给他送来针剂,他也曾有过一种猜测,他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取得永生的唯一一人。但是他能确定的是,无论他做或不做什么,那个人都能够找到他,而他摸了几十年的底,仍然摸不到任何头绪。
为了防止他的背叛,针剂每次只送来六个月的量,这也是他对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的交代,虽然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办法,不过是推门入桕罢了。倘若毁了唯一的实验体,他失去的是对馥汀兰的执念和佑护,而对方失去的是实验结果和一个庞大的布局。
他其实有些口渴,但是身体痛得令他无法翻动身体。一个蒙着脸的人突然走进来,他嘴唇哆嗦着扯出一个笑来,“这夏日的夜里也会有些冷,看来天然的身体与工具体的确不大一样。”
那人为他打了一针,并扶起他的身体,喂了两口水。
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个蒙面的人无比熟悉,可每次都是他即将奄奄一息时突然出现,他只能猜测,却毫无根据。
陈思源本想用一双眼死死的瞪着,虽瞪着,却瞳孔涣散,骤然昏昏欲睡。在马上失去意识前,他用尽全是力气伸手去拽下那人的面罩,看见了一张让他无比熟悉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