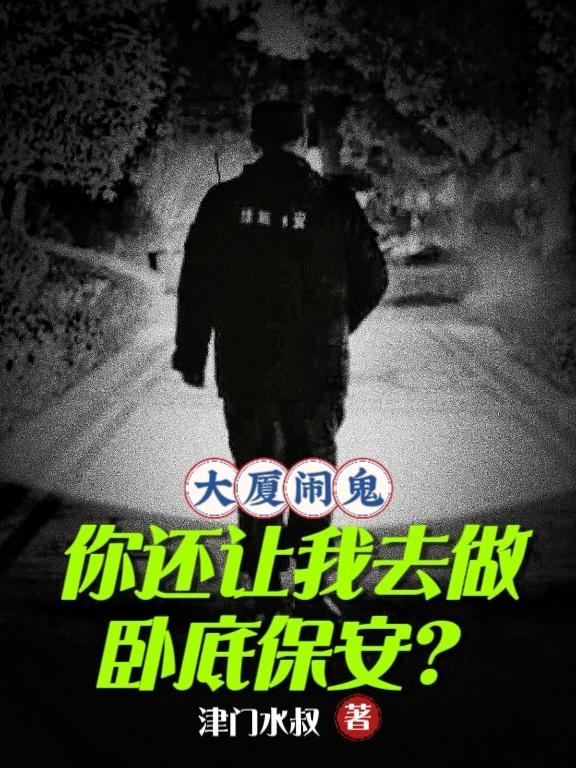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花开黎明 > 第 4 节 美玉无瑕(第1页)
第 4 节 美玉无瑕(第1页)
景元二十一年的隆冬,府里的大小姐从北境回了京。
她打了胜仗,救了太子,一时风头无两。
二小姐嫉妒她得了皇家的青眼,要我去给大小姐下毒。
她拿我妹妹威胁我,说我读过书,该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
是,我读过书,识过字。
我不但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还知道弃暗投明、明哲保身。
1。
我被卖到侯府时,将将十一岁。
府里的管事婆子见我识得几个字,模样也算清秀齐整,便将我往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培养。
我学了半年的规矩,被二小姐挑走,成了她书房里的研墨丫鬟。
二小姐是燕京有名的才女,府内外,人人都赞她才情斐然,温婉端庄。
提起宣阳侯府,百姓们大多只知二小姐,而不知大小姐。
哪怕大小姐才是府内唯一的嫡出。
就算有人提起大小姐,也大多是说她一介女儿身,非要抛头露面地往军营里钻,放浪形骸、不知检点。
直到这一年,北境的大小姐打了胜仗,为救太子,还伤了一条胳膊。
消息传回燕京,百姓们欢呼雀跃,口中的「放浪形骸、不知检点」就变成了英明神武、坚毅果敢、巾帼不让须眉。
书房里,二小姐撕碎了满地的宣纸,砸烂了一整套名贵的紫砂茶壶,又将那块儿松烟墨狠狠摔向我。
额头上流下的血糊着我的眼睛,我听见二小姐透着浓浓戾气和不甘心的声音。
「凭什么她就有这样好的运气?」
「没死在战场上就罢了,竟还救得太子,得了皇家的青眼!」
我在二小姐院子里待的这两年,日子并不好过。
寻常二小姐最爱往衣衫布料遮住的地方下手,这是她头一次如此失态,弄伤了我的额头。
我去往大小姐的院子前,二小姐当着管事婆子的面,给了我一整盒昂贵的白玉膏。
说是不单可以祛除疤痕,还可以使得肌肤柔滑、白似玉石,故名白玉膏。
管事婆子赞道:「二小姐便是这样善心了,她粗手粗脚地跌伤了额头,哪里就用得着二小姐这样名贵的药膏了?」
二小姐柔柔地笑:「不过十三岁的小姑娘呢,又要在我大姐姐跟前伺候,若是留了疤怎么得了?」
她穿着一身百褶如意月裙,清丽柔美如月中仙子,「阿瑾,你去了大姐姐哪儿,可千万要记得我的嘱托,」
我俯下身,恭恭敬敬地行礼:「奴婢省得。」
管事婆子也弯身一礼,躬身退出花厅,她领着我往大小姐的院落去。
大小姐喜静,她的院落在府中最偏僻的西园。
我跟着管事婆子行过月洞门,路过荷塘,又踏上弯弯绕绕的水廊。
如此走了快一刻钟,方才到了大小姐的院落。
坊间将上得战场杀敌的大小姐传成了女阎罗,说她定生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不然如何耍得动那近四十斤的大刀?
可见了面方知,传闻与事实的差距,就好比二小姐的菩萨面、蛇蝎心。
若说二小姐清丽如月中仙,那大小姐便高洁似莲上雪。
大小姐的性子和二小姐比起来,仿佛是两个极端。
二小姐素来爱笑,逢人便是一双盈盈笑眼,就连打我时,那沁了花汁似的红艳艳的唇角也是上扬着的。
大小姐不同。
大小姐不爱笑,人冷清,院子里也冷清。
那些新拨来的丫鬟们都怕她,见了她仿佛老鼠见了猫,问话时头恨不得能埋进地里,声音颤得不成调。
只有我敢近身去伺候大小姐的起居。
但她其实不惯被人伺候。
甚至我捧着浸过热水又拧干的帕子给她,大小姐还有些不自在。
想来也是,大小姐空有个宣阳侯府嫡长女的名号,可父母早逝,她孤零零一个长在北境,风吹霜打,野草一般,不似二小姐这样养在深闺里的富贵花。
可她又是带了伤的,伤在胳膊,包扎得严严实实,吊在脖颈上。
她只有一只手可用,有些必要的事情,还是得来人帮手才行。
我伺候大小姐穿衣、梳妆、换药,她从一开始的不自在,到后来渐渐习惯,若是有事需要帮手,她也会语气和缓地喊一声我的名字。
大小姐的脾气其实十分的好。
她除开必要的一些事,还是不惯让人伺候,因此院子里的下人们将手上的活儿做完,就会钻进房里躲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