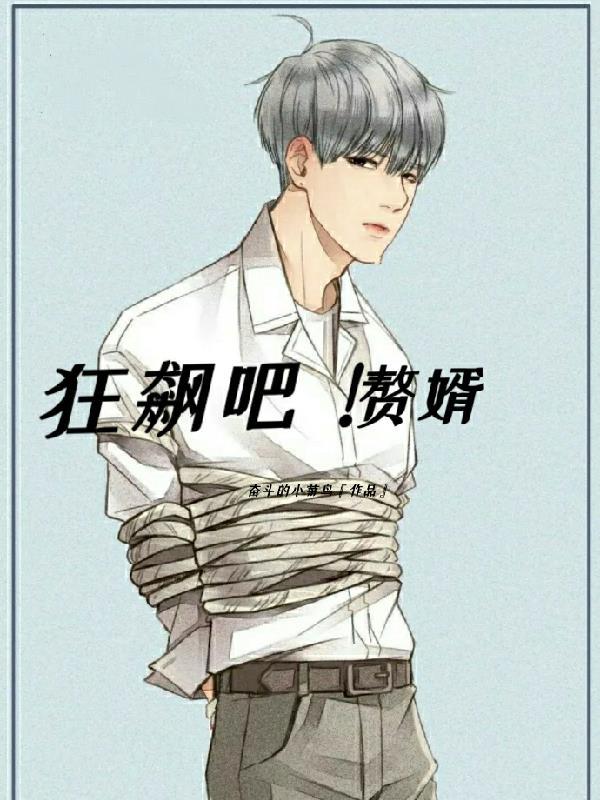69书吧>定风波作文800字中考 > 第86页(第1页)
第86页(第1页)
可他把问题抛向朝臣,看的便是阶梯之下众人的反应。
但一句问出,反而没人在此时贸然进言,皆是眼观鼻鼻观心,不愿做出头之鸟。
最后还是景行担了责,淡淡道:“回陛下,此事虽说法不责众,可牵头人定是要查上一查以示惩戒的,不然天下人人效仿,便成遗乱了。”
慕容燕淡淡地“嗯”
了一声,眼神一转:“太子,你说呢?”
近日太子频繁参政,早就做好被天子点名的准备,于是不慌不忙地说出了自己的腹稿:“邺城位居临安东北之地,富商人数便占了整个大渝的头筹。儿臣觉得,还是以安抚民意为主。父皇忙于政务,不能及时垂听民情本是常理,非我等之过。”
太子仁德的名声倒不是无中生有,眼下一番甩锅般的言论,听得慕容燕也是心情熨帖,连连点头。
从小培育的皇子,长成慕容燕期望的模样,不管是作为天子,还是一个父亲,想必都是极其欣慰的。
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便不能像太子说的那般,迂回处置了。
于是有顽固一派崇尚政权的,上前道:“回禀陛下,杜州府乃朝廷命官,被一群反叛的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焚烧而死,若不加以严惩,皇权的威严何在?”
谢璋隔着人群远远一望,竟是许久不曾上朝的于章。
于章是个顽固又贪心的主儿,平日里在皇帝面前却表现得无欲无求为国为民,但私底下死在他手中的人,简直可以从皇宫排到他的于府。
夏履生前因皇后在中的原由,与于章交好,可临头逼宫时,于章却及时脱身,没在其中掺和一脚,这才有眼下的苟延残喘。
于是于章便在朝中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眼下他突然站出,说出这一番话,怎么看都像心怀鬼胎。
可慕容燕倒觉得于章的意见与他相同,便也没多想,抬手便道:“那便按于卿说的做吧,牵头之人重罚,其他的人也要罚,大渝治国,从来都不是以人情为准的。”
宋徽站在百姓的角度,知此事慕容燕又想如同以前一样,重压百姓。可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在此时也说不上什么话,正天人交战间,有人先他一步,上前道:“陛下,臣有事禀报。”
是钟悦。
谢璋皱眉看向钟悦,然而他的方向看不到什么,于是视线流转间便停到了景行的身上。
景行安安静静地站在列,似乎是察觉到谢璋的视线,回过头冲他露出一个浅笑。
心有灵犀般,谢璋从这个笑意中,分辨出一种运筹帷幄的意味。
那边钟悦已开了腔:“杜州府一事生时,臣翻遍吏部官员登记在册的名案,现了一件怪异的事——臣并未在名册中查到任何关于杜州府的升迁事宜。臣便顺着查了下去,现他未有家族官爵继承,也并未参加过科举。”
若要在大渝在朝为官,要么世袭官爵,要么考取功名。若两者皆非,那便只剩一种可能——买官。
于章的脸色“唰”
得一声变成惨白。
谢璋几乎是一瞬间便明白了。
于章本着赚利的小心思,以为小小的一个州府之职翻不起多大的风浪,皇帝日理万机也查不到他的头上。哪知邺城的百姓闹出这么大的事,杜州府的官职非正当渠道得来的消息便随之浮出水面。
谢璋又忍不住看了景行一眼。
于章既然敢售卖官职,自然是做好了后续的收尾。而眼下被钟悦查出了其中的怪异之处,恐怕少不了景行的运作。可他这几个月忙里忙外,哪里来的时间布这么大的局?这场局中所生的事,又有多少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钟悦省去的半句话,慕容燕自然能领会。
一时之间,众人都能察觉出天子陡然上升的怒气。
他本就厌恶贪官横行,便将买卖官员一行看得十分之重,若有人大胆触摸到这一条,慕容燕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他。
可即便是事情败露,钟悦也没有证据证明官职售卖的幕后推手就是他于章。
于章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在一众官员屏息凝神之际,开口道:“原来杜州府一职来的不明不白,那邺城的百姓们倒是做了一件好事。”
话音一落,于章便察觉到满朝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他不明不白地咽了口气,接着道:“官职买卖一事实属胆大妄为,陛下,臣愿查清此事,为皇上分忧!”
谢璋听见景行微不可闻地出一声嗤笑。
这于章也算是个奇人,事情败露不将自己摘将开来,反而莽莽撞撞地顶上去,不知是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只见慕容燕沉默地摆动着手中的小鼎炉,而后抬起头,淡淡地说道:“那便交给你吧。”
这场心思各异的朝会,在于章揽下杜州府一案之时为尾声。可慕容燕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在答应于章的请愿后,又将钟悦派去,监察于章的一举一动。
于章一脸菜色地出了宫门,又听见慕容燕将景行叫去了御书房。
情理之中,景行随着人潮出了殿门,趁着无人注意,长袖下的手搁在谢璋的腰间揩了把油,便老神在在地去了御书房。
皇帝已在室内等他。
近日慕容燕身体时好时坏,连御书房都是满室的药材味。景行一进去,便见室中央摆了一个极大的鼎炉,鼎中冒出的袅袅烟雾与药材味混入一体,呛得他步伐有一瞬的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