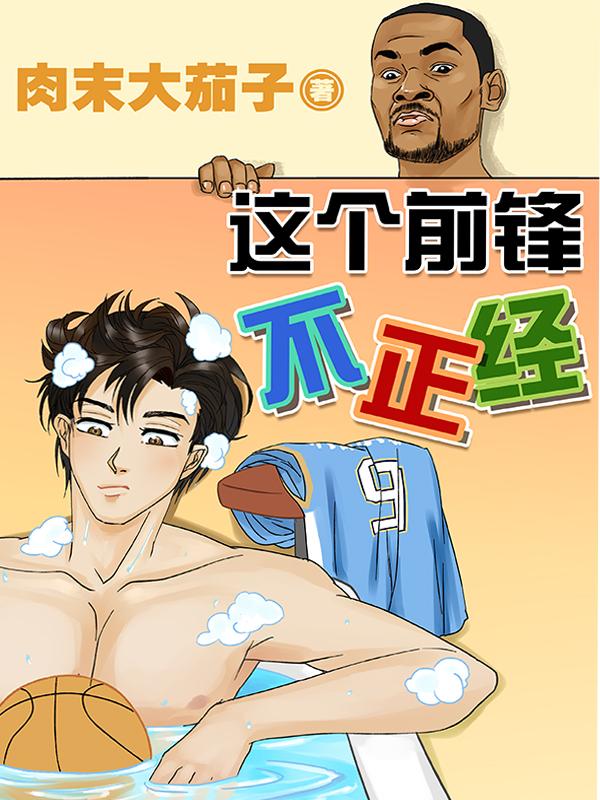69书吧>历代王朝顺序及年代图 > 刘家老三(第2页)
刘家老三(第2页)
,感到十分惊奇。因此,刘邦经常赊酒,日积月累,已经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这两个小本经营的妇道人家却主动“折券弃债”
,撕了账本,送了刘邦白喝。可真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想要交好刘邦。
王媪、武负虽是女流,倒还慷慨,一则因刘邦是恶少的头儿,不敢得罪;二则有他在此居住,他的朋友便要前来和他相聚,吃喝玩乐,一计算,得钱胜过往日数倍,二主妇暗暗称奇,所以刘邦要赊账,无不应允。刘邦见二妇肯赊账于他,暗自欢喜。有时自往独酌,有时邀客共饮,猜拳行令,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仰卧肆中,作长夜之眠。
二妇怕生意外,少不得守在身旁,供他驱使。刘邦虽说顽皮,还是童子之身,尚不知男女之事的妙处。
王媪不同,三十七八,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守着一个男人,一个英俊潇洒且又风流倜傥的大活男人,那心岂有不动之理?待到更深夜静,待到刘邦酣睡之后,总要伏下身子,在他额头、鼻尖、双唇上轻轻亲吻一番。
这一夜,刘邦睡眼蒙眬之中,忽觉脸上一阵奇痒,睁目一瞧,见王媪伸着一条香舌,在他脸颊上游来游去,又惊又喜又羞,忙闭了双目。
王媪自十七岁便随男人开店,模样儿俊,人又风流,二十一年来,睡过的男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个,可谓情场老手。刘邦控制不住,忽地一下坐了起来,搂住王媪纤腰,回了她一个长长的热吻。
王媪死了男人,已有半载,做梦都想找一个男人,刚才那番撩拨,自己也已动情不已。刘邦浑身瘫。他从来没有这么瘫过,也从来没有这么美过。自此之后,他方知道,在这大千世界还有比佳肴、美酒、赌博、游乐更美妙的东西——那便是女人。一天不碰,他便无精打采,如同患了大病一般。十几天了,大概有十三天吧,刘邦没有去武负酒肆光顾,武负感到奇怪,悄悄遣人打听,却原是王媪把刘邦给迷上了。没有了刘邦的光顾,这酒肆的生意一落千丈,怕是要不了三五个月,便要关门歇业。一旦这样,那日子可怎么过?
武负越想越是后怕。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武负也是女人,她渴望男人,渴望有男人爱抚、亲昵!可她不同于王媪,她出身于书香之家,家教良好,只因老爹得罪了一个屠狗的仇家,那仇家一把大火,把她家的房产变成了废墟,还杀了她的爹爹。迫于生计,她不得不嫁给一个开酒肆的掌柜。这掌柜生性怯懦,寡言少语,三棒槌打不出一个屁来。她看不起她的男人,也看不起中阳里所有的男人,当然,刘邦除外——还是那句老话,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只是年龄有些过于悬殊,自己少说也要长刘邦十四岁,不忍下手。长十四岁算什么?王媪长他几岁呀?十六岁!再说,论模样,王媪也不及我,没有我白,也没有我丰满,更没有我气质高贵。她能使刘邦屈从,我为什么不能?
于是,精心打扮一番,遣一个会说话的小厮,去请刘邦。在刘邦心中,王媪、武负原本占据着同等的位置,不能厚此薄彼,一请便至。自此之后,刘邦盘旋于两个女人之间,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不知不觉又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楚国大地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楚国地处华夏东南,疆域之大,在战国七雄中跃居第一。七雄者,齐、楚、韩、燕、赵、魏、秦。秦自商鞅变法,日渐强大,将韩、赵、燕、魏、楚、齐诸国次第灭去。其中尤以灭楚最为不易。
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灭魏之后,意欲伐楚,谋之于将军李信:“将军度伐楚之役,用几何人而足?”
李信对曰:“二十万足矣。”
复召老将王翦问之。翦对曰:“信以二十万人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人不可。”
秦王以翦为怯,置之不用。乃以李信为大将,蒙武副之,率兵二十万伐楚。楚王负刍闻之,拜项燕为大将,率兵二十余万,迎击李信。大战了三天三夜,李信败北,亡都尉七人,军士死者无数,没奈何向秦王告急。
秦王方知王翦所言不虚,乃亲造王翦之邸,愧声说道:“寡人深悔未听将军之言,致有李信之败。将军虽病,可为寡人强起,将兵一行。”
王翦谢曰:“老臣百病缠身,心力俱衰,请大王择贤将而任之。”
秦王摇头说道:“寡人之意已决,此行非将军不可,请将军莫要推辞。”
王翦不敢再拒,再拜对曰:“大王若是非要用臣不可,臣斗胆再进一言,伐楚之兵,非六十万人不可!”
秦王心中总以六十万人为多,辩解道:“寡人闻,‘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不尽行,未尝缺乏’。五霸威加诸侯,其制国不过千乘,以一乘七十五人计之,从未及十万之额。今将军必用六十万,古所未有也。”
王翦对曰:“古者约日而阵,结阵而战,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伤,声罪而不兼地,虽干戈之中,寓礼让之意。故帝王用兵,从不用众。今非昔比,列国交战,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逢人则杀,遇地便攻。杀人以万来计,攻城经年不克,是以农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册籍,势所必至,虽欲用少而不可得。况楚国地尽东南,号令一出,百万之众可具,臣谓六十万,尚恐不足,岂能减于此哉?”
秦王默想许久,叹曰:“非将军久经疆场,不能透彻如此,寡人听将军矣!”
遂以后车载王翦入朝,即日拜为大将,以六十万兵授之,仍用蒙武为副,大举伐楚。楚以项燕为将,率兵拒之。两军相持年余,王翦突然向楚起进攻,四战四捷,负刍被掳,项燕自杀,楚自此亡矣。按照常理,亡国之民,应该是运交华盖,矮人三分,刘邦不只逃过了这样的厄运,反乘乱而起,当上了泗水亭亭长。
在秦国,亭长是不入流的小官,所辖的范围,大约方圆十里。其职责一是治安警卫;二是传递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具有驿长的性质。
当然,处理亭内的民事也在他的职权范围。就这么一个芝麻大的小官,没有后台,没有银子,一般人也是很难弄到手里。
刘邦不是一般人。刘邦是一个浪儿头头,为争这个亭长,他的小兄弟给他凑了二十两银子,王媪、武负更是慷慨解囊,又凑了十二两。
单凭三十二两银子,刘邦也不一定就能当上亭长。他的竞争对手,除了沛县城中的曹无伤,还有一个雍齿。雍齿是雍家寨人,是专治无名恶疮膏药的传人,家中的财产,少说也值个五百两银子,若要斗富,刘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在这关键时刻,夏侯婴起了作用。夏侯婴老表的老表,认识沛县职县令。经他举荐,夏侯婴当上了职县令的车夫。职县令是秦人,且又贪财好色,为沛人所不容:或直造沛衙,或道中设伏,一心要取他的小命。夏侯婴为救他,伤了右肋,医治了三个多月才康复,自此职县令把他引为心腹。正因为职县令把夏侯婴引为心腹,夏侯婴才得以在他面前三番五次举荐刘邦。若没有夏侯婴的竭力相荐,就是再凑三十二两银子,刘邦也当不上亭长。刘邦走马上任,带了两个小兄弟,一个是卢绾,一个是周绁。
严格说,周绁不是他的小兄弟,带周绁上任完全是看他爹刘执嘉的面子。刘执嘉也是一个势利眼。原来对刘邦很鄙视,听说他谋得了泗水亭长之职,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遣他的小儿子刘交,去到武负肆中,将刘邦接回家来,设宴相贺,行前,还给了刘邦二百文钱,让他购置衣帽。这钱,尚不及他所收贺礼的十分之一。刘邦有钱可赚当然高兴。然而刘执嘉虽说出了点钱,却赚到了声望。一般来说,声望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买到了中阳里人给他上了一个太公的尊号,可以与卢绾的爷爷平起平坐了。
儿子年近三旬,尚是光棍一条,若在往日,刘太公并不着急,也不想为儿子操心。如今不同,儿子当了官,管着两千多户人家,不能没有妻室。于是,他便到处找人给刘邦物色。刘邦虽说做了官,但他的名声实在有些太差——浪儿、无赖,贪酒好色,不说暗地的姘头,单就公开的就有两位,还经常到娼寮中取乐,好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呀?差的他又看不上。一晃又是两个年头。泗水是条河,也是一个郡,郡因水而得名,郡治相县,距泗水亭一百余里。